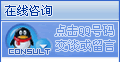| 專利輔助侵權制度中的法度邊界之爭 |
| 美國法例變遷的啟示 |
| 寧立志 武漢大學 教授 |
專利輔助侵權制度發(fā)達于美國。在美國,輔助侵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輔助侵權包括誘導侵權(Inducing Infringement)和狹義的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1]誘導侵權是指積極誘使他人侵犯專利的行為。而狹義的輔助侵權,又稱典型的輔助侵權(Classic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則僅指提供發(fā)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供他人侵犯專利之用的行為。在美國,對輔助侵權概念的使用經(jīng)歷了從廣義到狹義的演變,這一過程中的分水嶺即1952年美國專利法修正案。該修正案將誘導侵權與輔助侵權寫進法典,并明確將輔助侵權限定在狹義范圍之內(nèi)。自此以后,輔助侵權一般均在狹義意義上使用,
[2]而本文也是取其狹義。
輔助侵權制度之產(chǎn)生源于專利法中的一個漏洞,即如果某人不生產(chǎn)他人的整個專利產(chǎn)品,而故意制銷一種較完整的專利產(chǎn)品僅缺少某一組成部件的“非完全”產(chǎn)品,此時若根據(jù)專利一般侵權的判定原則,其行為并不構成侵權。為彌補這一漏洞,遂生輔助侵權制度,而對上述行為形成規(guī)制。舉例而言,如果甲的專利產(chǎn)品是一種由燈座與燈罩組成的改良煤油燈。而乙并未制銷整個煤油燈,僅僅制銷了作為該專利產(chǎn)品主要組成部分的燈座。這樣,由于乙并未生產(chǎn)整個專利產(chǎn)品,因此按照一般的專利直接侵權制度,其行為并不構成侵權。但毫無疑問,消費者購買該燈座后可以自行再購買一個燈罩,從而很容易地組裝出一個專利煤油燈產(chǎn)品,因此,乙的行為在實質(zhì)上與侵權無異。這種行為便是典型的專利輔助侵權行為。
[3]對這種行為加以規(guī)制的制度就是專利輔助侵權制度。就其本質(zhì)而言,輔助侵權制度系對專利保護范圍的擴張,即將專利的保護范圍從禁止他人制銷完整的專利產(chǎn)品擴張到禁止他人制銷作為專利產(chǎn)品主要組成部分的產(chǎn)品。而這種擴張直接動搖了專利法上的利益平衡,于是在美國,以權利濫用原則和修理原則為主的對抗勢力
[4]相應而生。雙方對抗的最終目的無非是為求得一個利益的平衡。而平衡向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美國,人們?yōu)槠鋬A注一個多世紀的智慧而至今尚無定論。美國輔助侵權制度成文化的主要推動者Giles S. Rich法官即感言道,“如果說專利法是法律中的玄學,那么輔助侵權問題則是專利法中的玄學”。
[5]下面,本文即對美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與權利濫用原則、修理原則之間沖突與平衡的錯綜復雜歷史加以考查,
[6]并將于此過程中就專利輔助侵權制度的范圍所形成的雖未臻明晰卻也有章可循的界限做一描繪,以期對我國輔助侵權制度的構建供輸比較法上的營養(yǎng)。
一、1952年前輔助侵權制度與權利濫用原則的沖突
美國第一部專利法頒布于1790年,而直到1870年,該法才迎來其第一次修正。但即使在1870年專利法案中,亦無只言片語提到過輔助侵權。自1870年以后的82年里,美國的專利法也未作修正。這即意味著,在幾乎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輔助侵權制度只是成長于普通法的判例法土壤中。
最早涉及專利輔助侵權的是1871年的Wallace v. Holmes
[7]案。該案中,專利權人的專利產(chǎn)品是一種由燈座與燈罩組成的改良煤油燈。而被告并未制銷整個煤油燈,僅僅制銷了該專利煤油燈的燈座部分。這樣,被告便很狡猾地規(guī)避了專利直接侵權制度的制裁,因其并未生產(chǎn)整個專利產(chǎn)品。但毫無疑問的是,燈座的購買者可以自行購買一個燈罩,從而很容易地組裝出一個專利煤油燈產(chǎn)品,因此,被告的行為在實質(zhì)上與侵權無異。而當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時,法院發(fā)現(xiàn)根本無法將該行為判為專利(直接)侵權,因被訴物品并未完全覆蓋專利物品的全部技術特征。值得慶幸的是,法院并未因此而止步,而是另辟蹊徑,認為較之于讓專利權人不現(xiàn)實地去追究購買者的直接侵權責任,更為合理的方法是允許其起訴實際竊取其專利利潤的銷售者,并進而判定銷售者應當與購買者一起承擔共同侵權的連帶責任。不過應當注意的是,該案并未提出輔助侵權的概念。而實際上,該案是被作為共同侵權而處理的。這也即意味著輔助侵權行為最初是被當作共同侵權行為而加制裁的,其逐漸脫離“共同行為”(Action inConcert)理論而發(fā)展成為一項獨立制度則是后話。
[8]于此角度觀之,專利輔助侵權其實與一般侵權法上的共同侵權行為具有同宗性。
[9]
從輔助侵權法律規(guī)制的歷史起源來看,該制度并非理論邏輯發(fā)展的產(chǎn)物,而系基于保護組合物品專利的現(xiàn)實需要而生。
[10]其必要性有三:其一,在一般情形下,起訴直接侵權者是不可行、不現(xiàn)實的;其二,即使在起訴直接侵權者是可行的情形下,追究輔助侵權者的責任對專利保護而言也是更為有效的;其三,專利發(fā)明作為一種知識產(chǎn)品較有形財產(chǎn)更易受侵犯,所以有必要給予更有力的保護。
[11]
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1894年的Norgan Envelope Co. v. Albany PerforateWrapping PaperCo.
[12]案中第一次提出了輔助侵權概念,但看起來卻對該新興原則心存疑慮。在該案中,其雖然承認了輔助侵權可以作為一種訴因,但卻否認了專利權人的救濟請求,并表示如果給予救濟的話將會使專利權人可以從一件非專利的普通物品上獲利。
15年后,也即1909年,當法院在Leeds&CatlinCo. v. VictorTalkingMachineCo.
[13]一案中再次遭遇輔助侵權問題之時,則更趨向于接受輔助侵權原則。在該案中,法院簽發(fā)了一道禁止輔助侵權的禁令。可以說,輔助侵權至此方才被確立為一項獨立的法律制度。但或許仍對該制度心存戒備,該案在確立輔助侵權制度的同時又給其戴上了一個“緊箍咒”。即通過區(qū)分“修理”(Repair)和“重造”(Reconstruction),及區(qū)分“修理用產(chǎn)品”與“構成專利產(chǎn)品之作用基礎的產(chǎn)品”,而將修理用產(chǎn)品排除在輔助侵權制度的適用范圍之外,進而達到限制輔助侵權制度的目的。
[14]
自此以后,始于對專利權擴張保護的輔助侵權制度開始活躍于美國法院之中,并很快逾越了合理的界限而打破了專利權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該原則于1912年的Henry v. A. D. DickCo.
[15]一案中隨著法院對搭售的許可態(tài)度而達到頂峰。在該案中,專利權人在銷售其專利物品時搭售了該專利物品的一些組成和關聯(lián)物件,而這種行為居然獲得了法院的認可。這即意味著,輔助侵權制度不但被作為專利權人保護其專利的防御武器,而且還被作為從其專利權范圍之外攫取不合理利潤的積極工具。
盛極而衰,世之常道。僅僅在五年之后,法院便在Motiom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Co.
[16]一案中將專利權濫用
[17]確立為一種針對直接和輔助侵權的抗辯事由,從而僅以專利權人實施了不公正濫用行為為由,拒絕給予專利權人以救濟。從此以后,美國法院便走上了對輔助侵權制度的限制之路。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判決使這條路線愈發(fā)的清晰, 1931年的Carbice Corporation ofAmerica v. American PatentsDe-velopmentCorporation
[18]案、1942年的morton SaltCo. v. G. S. SuppigerCo.
[19]案和B. B. ChemicalCo. v. El-lis
[20]案便是這條限制之路上幾塊重要的路碑石。在這幾個案件中,法院僅僅因?qū)@麢嗳舜嬖跒E用行為而直接終止了訴訟,而對被告是否侵權毫無興趣。這種態(tài)度在B. B. Chemical案中表現(xiàn)得尤其明顯。在該案中,專利權人提出被告所制銷的物品是除用于實施其專利方法之外無其他實質(zhì)性商業(yè)用途的“非常用物品”(nonstaple article),因此,其在該物品上的保護要求不會不合理地擴大其專利權的范圍,其不可能構成專利濫用。平心而論,這種觀點有相當?shù)暮侠硇裕绕涫瞧渲兴岢龅某S门c非常用物品的區(qū)分(the staple-nonstaple distinction)對以后的輔助侵權制度的合理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法院還是不予理會而拒絕給予救濟。走到這一步,法院在這條限制之路上似乎又有點走過頭了。由此造成的結果是,輔助侵權制度被逼得幾無容身之地。
而且權利濫用原則得勢不饒人,其繼續(xù)對輔助侵權制度施以限制,并于1944年的Mercoid案
[21]達到了頂峰。如果說在之前的案件中,輔助侵權制度尚有一絲游息,那到了Mercoid案,輔助侵權制度則幾乎被徹底架空了,其徒具形式而無實際作用。甚至有判例認為提起專利輔助侵權之訴本身即已構成專利權濫用,即使專利權人并沒有其他的權利濫用表現(xiàn)。
[22]由此可見,當時的法院給被告打造的防御之盾堅硬得幾乎足以抵擋專利權人射出的每一只箭,甚至連專利權人的搭弓之舉也被視為不法。
不過,即使在輔助侵權被普遍雪藏的年代里,也有一些判例發(fā)出了不同的且不容忽視的聲音,在這些案例里,法院以被告有侵犯專利權的故意為由判定輔助侵權成立。
[23]這些不同的聲音與Mercoid案所確立原則的對峙使得美國法院內(nèi)一片喧吵。
Mercoid案以后法院的認識不一給人們所帶來的只有困惑,輔助侵權制度還有一絲殘存嗎?如果有,那么輔助侵權與權利濫用的界限到底在哪里?這一系列的問題所引發(fā)的認識混亂,迫使以著名的Giles S.Rich法官為首的一些專利法領軍人物決定建議國會修改美國專利法,以對輔助侵權做出直接規(guī)定。這個建議最后被國會采納,專利法于1952年獲得了修正而增加了有關輔助侵權的條款。可以說, 1952年美國專利法頒布的一個主要動因就是為將輔助侵權原則成文化以平息相關爭執(zhí)。
二、1952年專利法的頒布及其平息沖突的努力
1952年修正案的頒布并非一路坦途,在其最終頒布之前,美國國會共舉行了三次聽證會以審議草案。
[24]第一次聽證會的舉行是在1948年,作為該次聽證會的倡議者,Rich法官極力主張通過立法來消除法律界關于輔助侵權與專利權濫用之間關系的混亂認識,但在司法部及汽車、農(nóng)用拖拉機的配件生產(chǎn)商的一片反對聲中, 1948年草案并未提交給國會;但倡議者們并沒有氣餒,在他們的要求下,國會于1949年舉行了第二次聽證會。Rich法官再一次挺身而出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極力主張通過給專利權濫用原則創(chuàng)設例外的做法,以使輔助侵權制度重獲新生,但這個草案同樣是在司法部的反對下擱淺了; 1951年,國會舉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聽證會。擔綱的依舊是Rich法官,他譴責Mercoid案在輔助侵權與專利濫用之間所引發(fā)的混亂,并痛陳輔助侵權制度在當時已形同具文,他為此所開出的藥方是對專利權濫用原則作一些例外限制以恢復輔助侵權制度的生命。但Rich不愧是一位高明的“醫(yī)生”,其深知“凡藥三分毒”,指出如果對專利權濫用原則的限制過于強苛則又會使輔助侵權制度滑向偏袒專利權人利益的深淵,這將會過猶不及。由此看來,Rich法官所主張的是一種平衡、折衷的方案,正如他本人所說,“看起來, (專利法)第271條c款頒布的重要理由就是為了在輔助侵權原則與專利濫用原則之間達成一個和解”。
[25]在一片倡議之聲中,鑒于在輔助侵權的適用范圍上所存在的無盡迷惑,國會最后決定將輔助侵權原則予以成文法化,以平息有關的爭執(zhí)和混亂。于是,美國1952年專利法修正案便宣告誕生了。
該法第271條的具體規(guī)定如下:
§271.專利侵權
(a)在美國境內(nèi)及專利的有效期內(nèi),任何人未經(jīng)授權而制造、使用或銷售專利發(fā)明,則構成專利侵權,本條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
(b)任何人積極誘使他人侵犯專利則應承擔侵權責任。
(c)任何人出售某項專利機器、產(chǎn)品、組合物及合成物的組成部分或者出售用于實施某項專利方法的材料或裝置,從而構成發(fā)明的重要部分,且他明知其所販賣者是為侵犯專利權而專門制造的或者專門供侵犯專利權使用的,而且這樣的部件、材料或者裝置不是具有實質(zhì)性非侵權用途的常用物品或商品,則其應承擔輔助侵權的責任。
(d)因?qū)@謾嗷蜉o助侵權而本應給予救濟的專利所有人不應因其實施了下列行為中的一項或多項而被拒絕給予救濟或被視為權利濫用或不正當擴張其專利權利:
(1)從某種行為上獲利,這種行為若未經(jīng)其同意而實施便會構成專利輔助侵權;
(2)許可或授權他人實施某種行為,這種行為若未經(jīng)其同意而實施便會構成專利輔助侵權;
(3)為對抗專利侵權或輔助侵權而尋求其專利的實現(xiàn)。
由上述條款可以看出,專利法第271條將專利侵權分為兩大類,即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其中(a)項規(guī)范的是直接侵權, (b)、(c)兩項分別規(guī)定了兩類不同的專利間接侵權類型,即誘導侵權和輔助侵權。而(d)項則通過明確規(guī)定三類行為不被視為濫用而對專利權濫用原則做了一定的限制以劃清輔助侵權與專利權濫用的界限。
根據(jù)(c)項的規(guī)定,輔助侵權的構成要件有下列4項: (1)所販賣者系某專利物品的組成部件或用于實施某專利方法的材料或裝置; (2)所販賣者系發(fā)明的重要部分; (3)所販賣者系為侵犯專利權而專門制造的或者專門供侵犯專利權使用的,且販賣人明知這一點; (4)所販賣者不是具有實質(zhì)性非侵權用途的常用物品或商品。尤值一提的是,大概出于對輔助侵權制度不當擴張的過于謹慎的提防心理,該條(c)項“實際上通過三種方式,即要求嫌疑物品是‘專門制造的或?qū)9┦褂玫摹皇浅S梦锲坊蛏唐贰约安皇恰哂袑嵸|(zhì)性非侵權用途’,而不厭其煩地要求嫌疑物品必須沒有非侵權之實質(zhì)用途”。
[26]正如立法者自己所稱,他們明確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將那些出售普通商品、常用物品的人們排除在外。
[27]
而就該條(d)項的規(guī)定來看,其明確將三類行為排除在權利濫用之外: (1)從某種行為上獲利,這種行為若未經(jīng)其同意而實施便會構成專利輔助侵權。該款規(guī)定將此類行為排除適用權利濫用原則即意味著,專利權人不單可以從專利權利要求所賦予的專利壟斷權中獲利,而且還可通過出售該專利產(chǎn)品中未被授予專利的組成部件而獲利。這其實已認可了專利權人可在某些情形下將其專利權擴及未被授予專利的組成部件之上; (2)許可或授權他人實施某種行為,這種行為若未經(jīng)其同意而實施便會構成專利輔助侵權。該款規(guī)定其實是第一款規(guī)定的延續(xù),根據(jù)該款規(guī)定,專利權人不但可以通過自己出售專利產(chǎn)品中未被授予專利的組成部件而獲利,還可以通過許可他人出售而收取許可費的方式來獲利; (3)為對抗專利侵權或輔助侵權而尋求實現(xiàn)其專利的行為。這種行為,其實主要指的便是提起侵權之訴的行為。之所以要將此類行為明確排除于權利濫用原則的適用范圍之外,其實是針對前述判例將專利權人提起輔助侵權之訴的行為直接認定為權利濫用的極端觀點而做出的立法否定。
據(jù)前述觀之, 1952年的美國專利法修正案為調(diào)和專利輔助侵權制度與權利濫用原則之間的沖突可謂用心良苦。但在美國,立法對司法的影響力向來不容樂觀,其普通法傳統(tǒng)使得立法往往從其誕生之時便置身于司法敵意之中。
[28]因此,即使是在專利法第271條頒布以后,律師及其顧客,以及法院均怠于反應,他們對如何解釋其中的一些條款,尤其是如何認識輔助侵權制度與權利濫用原則的關系并無確信。因此,立法者調(diào)和沖突的良好初衷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現(xiàn)還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三、法院對1952專利法第271條的解釋及仍未平息的沖突
1952年專利法頒布之后,直至1961年的AroMfg. Co. v. ConvertibleTopReplacementCo.案(Aro I)
[29]及1964年的AroMfg. Co. v. ConvertibleTopReplacementCo.案(Aro II)
[30](即著名的雙Aro案),聯(lián)邦最高法院才遭遇到第271條。在這兩個案件中,最高法院對于第271條(c)款的規(guī)定做了一定闡釋,但卻并未涉及對(d)款的解釋,也即并未觸及輔助侵權制度與權利濫用原則的沖突這一最棘手的問題。
在Aro I案中,法官們功過各半。就其功而言,法院對第271條(c)的規(guī)定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即認定輔助侵權的成立必須以直接侵權的存在為條件,從而在據(jù)法條條文所能推導出的4項要件之外又發(fā)展出了一個要件,而這個要件無疑是非常必要的;而就其過而言,該判決認為,不管被告所販賣的物品是否是專利組合物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不管在專利物品上更換這一販賣物品的成本和難度有多高,專利權人均無權壟斷該物品。
[31]而這種無視被訴物品對專利物品的重要性的觀點顯然是與立法意圖相左的。這種與立法意旨背道而馳的解釋無異于向本趨平息的爭論之焰又澆了一瓢油,是其過。法院最后認定,購買者更換某個部件的行為是一種修理行為而不構成直接侵權,進而判定被告提供更換部件的行為不構成輔助侵權。
[32]
而到了Aro II案,案件的焦點因案情的不同而發(fā)生了變化。在此案件中,涉及到的主要問題是對第271條(c)款所規(guī)定的行為人主觀認識要件的解釋。就法條原文來看,其要求行為人須“明知其所販賣者是為侵犯專利權而專門制造的或者專門供侵犯專利權使用的”,而問題就出在對于“明知”的范圍的解釋上:是要求行為人僅僅知道其所販賣物品是專利物品的組成部分,還是要求行為人不但知道其所販賣之物品是專利物品的組成部分,且知購買者系將物品用于直接侵權。顯然,依據(jù)后一種要求所構建的主觀要件更為嚴格也更為合理,而這也正是法院所最終采納的見解。
雖然在雙Aro案中,最高法院涉及到了第271條(c)款的解釋,但由于案情并未關涉輔助侵權制度與權利濫用原則的正面交鋒,二者的沖突在輔助侵權成文法化后將會如何演變,人們?nèi)匀徊坏枚_@種令人矚目的交鋒直到1980年的Dawson Chemical v. Rohm&Haas一案
[33]才姍姍而至。
在Dawson案中,這種交鋒集中在專利權人的搭售行為是否構成權利濫用這一問題之上。而對于該問題, 1952年專利法第271條(d)款所列的三類情形并無明確規(guī)定,這樣就給輔助侵權原則與權利濫用原則的交鋒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被告認為專利權人拒絕向其許可專利且實施了搭售行為,這即已構成了專利權的濫用,進而以此作為抗辯。但法院并不贊同其主張,并認定,雖然專利權濫用原則仍可作為一種可行的抗辯手段,但專利權人不應僅因其將專利權擴張到非專利物品上而被判“本身”(per se)權利濫用。這即意味著搭售并非本身違法,而應視具體情形而為個案分析。最后,法院認定專利權人不構成權利濫用,并判定被告承擔輔助侵權責任。該判例的重要性在于,其對本身違法原則的否定為后來1988年專利法修正案處理輔助侵權與權利濫用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啟發(fā)。
從上述幾個案例可以看出,在1952年專利法頒布之后,雖然輔助侵權制度已成文法化,但法院的解釋仍有搖擺。而且由于制定法規(guī)范的封閉性,在一些未為規(guī)定的特殊情形下,仍需借助法官的衡量而為判斷。因此,即使是在輔助侵權制度成文法化后,輔助侵權原則與權利濫用原則之間的沖突仍未完全平息。
四、1988年修正案的頒布及其對沖突的模糊處理路徑
1952年專利法在1984年、1988年、1992年、1994年及2003年受到了多次修正。
[34]其中,涉及輔助侵權制度實質(zhì)修正的主要有: 1984年的部分修正和1988年的部分修正。
1984年關于輔助侵權制度的修正是在第271條下增加了(f)款規(guī)定。
[35]該款規(guī)定的頒布是為了彌補輔助侵權制度的一個漏洞,即根據(jù)1952年專利法修正案的規(guī)定,在美國國內(nèi)制銷專利物品的重要組成部件而在美國國外組裝的行為無法被判定為輔助侵權。因輔助侵權的成立須以直接侵權為前提,而在上述情形下,最后的專利物品的組裝是在不受美國專利法管轄的國外完成的,因而其在美國國內(nèi)不構成直接侵權,從而輔助侵權也無從談起。為了應對這種法律規(guī)避行為, 1984年的專利法修正案便增加了第271條(f)款而彌補了上述法律漏洞。
雖然1984年修正案所增設的第271條(f)款關涉了輔助侵權制度,但卻并未就輔助侵權制度的核心難題做出規(guī)定。真正直面輔助侵權原則與權利濫用原則沖突的當屬1988的專利法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在第271條(d)項下增設了(4)、(5)兩項
[36]不視為權利濫用的例外規(guī)定:
(d)因?qū)@謾嗷蜉o助侵權而本應給予救濟的專利所有人不應因其實施了下列行為的一項或多項而被拒絕給予救濟或被視為權利濫用或不正當擴張其專利權利:
……
(4)對專利許可或使用任何專利權利的拒絕;
(5)以購取另一專利的許可或權利或者購買一項獨立的產(chǎn)品作為專利權利許可或?qū)@锲烦鍪鄣臈l件的行為,除非根據(jù)具體情形,專利所有人在附條件許可或銷售的專利或?qū)@a(chǎn)品的相關市場上擁有了市場力量。
對于第(4)款我們無需多言,而第(5)款的規(guī)定似乎否定了先前一些判例和司法部的某些政策中認定搭售為本身違法的觀點。可以說這兩款規(guī)定是對前述Dawson案的回應,而將該案就搭售行為所提出的合理分析原則
[37]予以立法固定化。一廢一立之下,立法意圖已甚明顯。但立法者為了限制法官在司法中對上述意圖的背離,以確保立法意圖能得以貫徹,甚至不厭其煩地將其意圖明確宣示道:這一建議的潛在原則是消除任何視一定的搭售行為本身違法或自動推定其為權利濫用的殘余。
[38]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款的規(guī)定中,使用了“根據(jù)具體情形”、“市場力量”及“相關市場”等概念,這些概念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反壟斷法。而事實上,關于1988年修正案不容忽視的一段歷史是,在這個正式名稱為“專利濫用改革案”修正案之前,參議院曾提出了一個“知識產(chǎn)權反壟斷保護案”的提案。后者主張只有在違反了反壟斷法的情形下才構成專利權濫用。但這個將權利濫用與反壟斷法直接掛鉤的提案遭到了眾議院的反對,無奈之下,參議院才被迫與眾議院達成妥協(xié),即暫時頒布(4)、(5)兩款。而即使在這個妥協(xié)方案中,透過上述反壟斷法概念的運用,我們也可以依稀看到反壟斷法的身影。這是否代表了專利權濫用原則的一個走向,我們將拭目以待。
簡單而言,在1988年修正案中,立法者似乎看到了在輔助侵權和權利濫用之間劃定一條明確界限的困難性,從而改采了一種更為模糊也更為現(xiàn)實的處理路徑,即授權法官們在個案審判時具體判定是否構成權利濫用。該修正案所要明確表達的一點是,任何關于搭售是否屬于專利權濫用的判斷都不能徑直依本身違法原則做出,而應考慮具體情形而為合理分析。
五、修理原則與輔助侵權制度的沖突
其實,權利濫用原則無非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的名義對專利權加以限制的一種手段,雖其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直充當著限制輔助侵權制度的主力軍,但這并不意味著于其之外即不存在其他限制手段。在美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歷史上,還存在另一個同樣引發(fā)了無盡爭議的限制手段———“修理原則”。
根據(jù)修理原則,如果專利權人擁有一項“A+B+C”的組合物品專利,而該專利物品的購買者若在使用過程中發(fā)現(xiàn)其中的A部件損耗了,則其有權將A部件予以更換。因為專利權人一旦將專利物品售與購買者,即給予了其使用該專利物品的默示授權(Implied License),而“修理”當然在該使用范圍之內(nèi),因此,購買者更換專利物品某個部件(一般是易耗損部件)的行為將被視為對專利物品的修理而不構成侵權。
[39]而如果更換A部件的行為不構成直接侵權,那第三人提供該A部件的行為則當然不構成輔助侵權。由此可見,修理原則無非是通過證明輔助侵權之前提(直接侵權)的不成立來否定其成立,此可謂“釜底抽薪”之策。
其實在歷史上,修理原則早已有之,其在早期主要是被用作直接侵權的抗辯事由。但即使是在輔助侵權問題上,修理原則也非新面孔,在前述關于輔助侵權的許多案件中其實均有其身影,只是早期人們投向輔助侵權的目光主要為權利濫用原則所吸引而不作他顧。然而,雖然在歷史上修理原則所引發(fā)的爭議不像權利濫用原則那樣引入矚目甚至影響立法進程,但其與輔助侵權制度之間的沖突及爭議絲毫不遜于權利濫用原則。
在一般情形下,修理原則其實并不會與輔助侵權制度形成沖突。因為修理一般只是更換專利產(chǎn)品中某個易耗損的細小部件,而提供這種不構成專利物品重要組成部分的細小部件的行為同樣也不會構成輔助侵權。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沖突則是不可避免的,即當專利產(chǎn)品中某個重要或核心部件是易耗損物品時,若從輔助侵權角度來看,提供這種部件的行為無疑將會構成輔助侵權;而從修理原則角度視之,如果法院認定更換該部件的行為不屬于合法的修理行為則尚無沖突可言,但如果法院認為該更換行為屬于合法之修理行為的話,則根據(jù)修理原則,提供該更換部件的行為將免于承擔輔助侵權責任,于是修理原則與輔助侵權制度之沖突遂生。由是觀之,修理原則是否會與專利輔助侵權制度形成沖突,需視乎“修理”的范圍而定,即需系于對如下問題所作的回答:“更換構成專利物品重要組成部分的部件”之行為是否在合法的修理范圍之內(nèi)。而這一關于修理范圍的判斷實際上正是美國專利法上著名的“修理/重造(Repair/Reconstruction)”之爭的核心問題。
之所以會有“修理/重造”之爭,是因為將專利物品的某個無關緊要的易耗損部件予以更換固然屬于“允許的修理(PermissibleRepair)”范圍之內(nèi),但如果“修理”超過了一定的界限而實際上重新制造了一個專利物品,則淪為了“禁止的重造(Forbidden Reconstruction)”。而允許的修理與禁止的重造之間在很多情形下往往僅有一線之隔,對二者加以明確區(qū)分無疑是非常困難,而這個問題也讓美國法院的法官們極為頭痛。可以說,一直以來,在合法的修理與非法的重造之間都缺乏一條明確的界限。
在美國,第一個涉及修理與重造之界分的案例是1850年的W ilson v. Simpson
[40]案。在該案中,原告的整個專利產(chǎn)品的使用壽命一般是幾年,而其中的一個“切割刀”部件卻只有平均60-90天的使用壽命,這也即意味著該部件是易耗損的。據(jù)此,法院認定由于切割刀屬于易耗損物品,因此被告自行更換切割刀的行為屬于修理行為而不構成侵權。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案的判決書中,法院明確表明:對已耗損部件的更換屬于合理的修理,“即使這是對專利組合物品中基本部件的更換”。
[41]而根據(jù)這種明確不考慮更換部件是否構成整個發(fā)明之核心的觀點,任何第三人提供專利物品之重要組成部件的行為,將會僅因該部件是易耗損的而不構成輔助侵權。顯然,這種結論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畢竟所提供更換的是專利物品的核心部件。由此看來,即使依據(jù)最初的相關判例對修理與重造界分所采的觀點,修理原則即已構成了對輔助侵權制度的不當限制威脅。但如果說該案對輔助侵權制度所形成的僅僅是一種威脅的話,那一個多世紀后的AroI案
[42]對該制度所構成的則是一種現(xiàn)實的消解。
其實在1961年的AroI案之前,美國最高法院還處理過其它幾宗涉及修理與重造區(qū)分問題的案件,但一直未能突破W ilson一案所形成的判決觀點。這種突破直至AroI案才形成。AroI案是美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案件,其不單涉及前文所述之對第271條(c)項的解釋,而且還涉及到修理與重造的區(qū)分問題,其于后者的意義較于前者更為重大。就該案所關涉修理與重造的區(qū)分而言,基于任何人都不能將其專利壟斷權擴及專利物品中某一未授予專利的組成部件上的認識,該案的判決明確表示:除非所有的部件同時被更換,則任何更換專利產(chǎn)品某一組成部件的行為均屬于合法的修理行為,即使所更換的部件是專利產(chǎn)品的重要甚至核心組成部分,或者更換該部件是高成本及高難度的,甚至所更換的部件不是一個易耗損的部件。由此看來,該判例對W ilson案所形成的突破是令人吃驚的。在W ilson案中,法院還只是不考慮所更換部件是否構成專利產(chǎn)品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AroI案中,法院則還排除了對更換成本及難度的考慮,甚至還排除了對所更換部件本身性質(zhì)的考慮,即不考慮該部件是否屬于易耗損部件,從而將非法的更換行為情形僅限于對專利產(chǎn)品全部部件的“同時”更換這一狹窄范圍之內(nèi)。這無異于授予專利部件物品的合法擁有者一種“絕對”權利,使其可以置換專利產(chǎn)品中幾乎全部的部件而擁有一件幾乎全新的專利產(chǎn)品,并美其名曰“合法修理”而不構成侵權。這對輔助侵權制度的消解作用無疑是致命的,因為原本構成輔助侵權的第三人只需確保其提供對象是專利部件物品的合法擁有者即可完全免除輔助侵權責任。可以說,修理原則發(fā)展至此,已完全打破了輔助侵權制度上的利益平衡,從而形成了對輔助侵權制度的過度限制。
撇開外界對該判決的批評不說,即使在最高法院審理該案的九位法官內(nèi)部對此亦分歧殊巨。尤值注意的是,該判決是以九位法官中5人贊同、4人反對的微弱多數(shù)做出的,且5人中還有一名法官(Bernnan法官)雖贊同最終結果卻不贊同判決在修理與重造區(qū)分上所采的觀點。Bernnan法官在其見解書中即指出,該判決對修理與重造之區(qū)分所采的方法顯然是不合理的,因其將非法重造的范圍限制得過于狹窄。Bernnan法官與其他4位持少數(shù)意見的法官均認為區(qū)分修理與重造需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這包括:所更換部件較之于整個專利產(chǎn)品的使用壽命、所更換部件對于整個發(fā)明的重要性、專利權人及購買者對于更換某該部件是否屬于修理的一般認識及所更換部件是否易損耗等其他因素。由此看來,該判決對修理與重造之區(qū)分所確立的原則可謂天生即具爭議。
如果將前述判決的多數(shù)意見把非法重造僅限于“同時更換全部部件”這一唯一情形的做法稱之為“單一測試法”(SingleTest),那該案中的少數(shù)意見所主張的區(qū)分方法則可稱為“多因素法”(Multi-factorAp-proach)。比較而言,后者較前者顯然更為合理。
[43]
由于該案所確立的“單一測試法”自產(chǎn)生之初即已極富爭議,因此,該判決給修理與重造之區(qū)分所帶來與其說是一個明確答案,毋寧說是一團毒霧。對此,外界的批評不絕于耳。美國專利協(xié)會對此忿忿不平,更不用提理論界對此的沮喪與不滿。
[44]其實,與權利濫用原則運用的過猶不及一樣,法院對修理原則的過度擴張無疑抽取了原先加諸于發(fā)明之火上的“利益之薪”,從而在根本上背離了專利法上的利益平衡。而這在專利權人當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甚至有人據(jù)此預測了組合物品專利的死亡,專利權人紛紛通過對修理與重造區(qū)分的“私約化”(Privatization)來明示購買者的使用權范圍而欲圖排除該判例規(guī)則的適用。
[45]
而即使在美國法院那里,該區(qū)分方法也不受歡迎,只是懾于該判例的先例效應而多予遵從,而下級法院亦陽奉陰違地發(fā)展出一些避免適用該區(qū)分法則的理論。
[46]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ofAppeals forFederalCircuit)
[47]近期的一些判決來看,其已開始挑戰(zhàn)該適用有年的“單一測試法”。
[48]該法院在1994年甚至明確表示,由于專利發(fā)明的復雜多變性,任何試圖為修理與重造的區(qū)分劃定一條明確界限的嘗試都是不切實際且不明智的,任何一個案件都應根據(jù)所有具體情況來加以判定。
[49]由此看來,該法院已公開反對最高法院在AroI案中所確立的“單一測試法”,轉而支持“多因素法”。但下級法院的這一嘗試在聯(lián)邦最高法院那里將會遭遇如何的態(tài)度至今尚不得而知。因此,關于修理與重造的區(qū)分在美國仍不甚明確。
總之,修理與重造的區(qū)分是一個需要平衡把握的問題,但一直以來美國法院即存在擴大適用修理原則的趨勢,及至AroI案更是達致巔峰。這種趨勢嚴重地擠榨了輔助侵權制度的生存空間,打破了專利法上的應有平衡。所幸的是,美國下級法院已開始意識到這一嚴重的失衡狀況,并做出了一些試圖回復平衡的努力。但總的說來,美國法院在輔助侵權制度與修理原則的沖突上更多地偏向了后者從而形成了對前者的過度限制,這一狀況至今尚未有大改觀。
縱觀上述歷史,如果用天平來代表美國法院的態(tài)度的話,那么可以說在早期,這架天平過分傾向于對專利權人利益的保護而失去了平衡,之后在社會公共利益這一砝碼的相反作用下,天平又迅速回復并逾過了平衡點而傾向另一個極端。這個時候,如果一方面要使法院這架天平盡快回復平衡,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處于永無休止的不平衡狀態(tài),就必須有一只巨手終止天平的搖擺,使其回復平衡。這個時候,立法者伸出了這樣一只巨手,頒布了1952年專利法修正案。但該法案的頒布者很快便遺憾地發(fā)現(xiàn),其所伸出的巨手一旦隨立法活動的結束而撤回之后,由于解釋的不一致及新情況的出現(xiàn),天平又開始了搖擺。雖然已無大幅波動,但小幅的搖擺仍難避免。最后,立法者也不得不接受這一現(xiàn)實,容忍其小幅擺動。并在1988年的修正案中改采一種更模糊、更彈性的立法模式,從而授權法官在一定范圍內(nèi)根據(jù)具體情況對輔助侵權制度和權利濫用原則二者加以平衡。此時,法院這個在輔助侵權制度與權利濫用原則的對立作用下晃悠了一個多世紀的天平似乎已趨平定。但一波仍漪,一波又起。隨著修理原則在一些晚近案件中的過度擴張,該原則已漸顯崢嶸,并逐漸消解了輔助侵權制度。而最近的一些判例又對該過度擴張趨勢提出了質(zhì)疑。由此看來,法院這架天平似乎將又無寧日了。但其在專利輔助侵權制度與修理原則的對抗下將會有多大幅度的搖擺,我們尚無法得知。或許有一天,當天平晃動得叮當大作而驚動了立法者之時,其又會伸出一只巨手,試圖使其回復平衡。同樣的,當巨手一旦撤回,搖擺或許又將開始。
凝定思緒,任由歷史爭吵之聲漸遠,一個深層問題卻浮現(xiàn)腦際而揮之不去,即在歷史的巨幕之后牽動著這一個多世紀沖突的究竟是什么?當我們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表象,而直索沖突的根源之時,我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其實這一切只不過是根源于對“專利發(fā)明中未授予專利的組成部件(Unpanted Component)”這一領土的爭奪而已。回觀歷史,作為專利權人擴張保護其利益的一項新興制度,輔助侵權制度無疑越過了專利權利要求書所劃定的傳統(tǒng)邊界而將“未授予專利的組成部件”這方疆土納入了自己的版圖。面對入侵,社會公共利益遂在權利濫用原則與修理原則的領軍下,奮起反抗。之后的歷史便不過是圍繞著這塊爭議土地所展開的你爭我奪而已。其忽而由專利權人利益所控占,忽而又轉而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占領區(qū)。為平息沖突,立法者與司法者則在其中極盡斡旋調(diào)停之能事而試圖使二者共享這塊土地,盡管他們就邊界線的劃定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和解方案,但沖突卻仍然不可避免,充其量只是規(guī)模稍小而已。而且令人沮喪的是,這條邊界線似乎永遠不可能劃定得清晰無爭。由是觀之,圍繞著輔助侵權制度所展開的一切爭執(zhí)之核心無非是保護專利權人利益多一點,還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多一點的問題。簡而言之,即二者的平衡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是輔助侵權制度所需面對的,更是專利法乃至整個知識產(chǎn)權法中亙古不變的一個主題。而歷史似乎一直以其特有的方式告訴人們:絕對之靜態(tài)平衡是不存在的,動態(tài)之平衡才是真實的歷史生活。
六、美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上的利益平衡歷史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目前尚無專門的專利輔助侵權制度,但在實務中相關案例已在不斷涌現(xiàn)。就目前的一些司法判例來看,我國法院是將專利輔助侵權作為教唆、幫助侵權而用共同侵權制度加以處理的。
[50]但在相應立法缺位的情況下,司法實踐的做法往往缺乏統(tǒng)一性,使得專利輔助侵權案件的處理遠未形成成熟的制度。因此,對專利輔助侵權進行立法具有現(xiàn)實緊迫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國在法治化的道路上,可以充分發(fā)揮后發(fā)優(yōu)勢,借鑒他國的歷史經(jīng)驗以為我用。而上述美國輔助侵權制度的發(fā)展歷史無疑可為我國相關立法提供諸多啟示和借鑒。
(一)制度模式的啟示———應對專利輔助侵權進行專門立法
從美國歷史上對專利輔助侵權處理的模式來看,最初是運用一般侵權法上的共同侵權理論來加以解決的,但是這一處理模式很快便在后來的判例中被拋棄了,之后美國立法和司法逐漸發(fā)展出了一套專門的輔助侵權制度取而代之。由此可見,在專利輔助侵權制度的模式上,美國走過的是一條從共同侵權模式向?qū)iT性專利輔助侵權制度模式的轉變之路。這種歷史的轉變可謂是專利輔助侵權特殊性驅(qū)使之必然。其實,就輔助侵權的本質(zhì)而言,其的確是一種共同侵權,但它同時又是一種極為特殊的共同侵權。對專利輔助侵權的判斷具有高度的專業(yè)性,涉及對專利權人利益和一般社會公共利益的衡量,其中的具體制度問題非常復雜,從而超出了一般共同侵權理論所能處理的范圍。正因如此,美國輔助侵權制度便在歷史發(fā)展中逐漸從共同侵權制度模式中獨立出來,形成了一套專門的理論。由此可見,專門性的輔助侵權立法模式應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共同侵權模式充其量只是一種歷史的過渡形式。在美國之后,歐盟、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匈牙利、冰島、挪威、芬蘭、立陶宛、韓國等國家或地區(qū)先后在立法中獨立設計出專利間接侵權制度,
[51]將輔助侵權的應對從共同侵權制度中獨立出來也證明了這一點。
就我國而言,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司法實踐界對是否應當設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的認識都還存在著分歧。認為有必要專門設立該制度的一般認為專利輔助侵權制度所針對的是專利侵權中的特殊情況,而這類特殊情況實際上與共同侵權的情況有著較大的區(qū)別,只有獨立設計專門的專利輔助侵權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并有助于維護技術市場正常競爭秩序。
[52]認為沒有必要專門設立該制度的則認為該制度很難準確區(qū)分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界限,容易助長法官偏袒專利權人之思想,且國內(nèi)輔助侵權案件出現(xiàn)得并不足夠多,共同侵權法律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應對已有的大部分案件,故無須單獨設立該制度;輔助侵權的相關理論在我國也不存在適用的環(huán)境和條件。
[53]后一觀點所闡述的理由應該說是有所偏頗的,案件的多少、制度實施的效果等并不應該成為是否進行立法的理由,美國輔助侵權制度的發(fā)展歷史表明,制度的設計主要是基于實踐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則是體現(xiàn)為當出現(xiàn)輔助侵權時是否能找到準確的法律依據(jù)以對相關權利人的權利進行認定和保護;制度實施的效果是受到多種因素影響的,能產(chǎn)生良好效果的法律制度的確立需要以該制度已經(jīng)存在為前提,且任何制度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和完善。隨著專利制度中專利權保護實踐的發(fā)展,我國現(xiàn)行法中關于共同侵權的聊聊數(shù)款之一般性規(guī)定根本無法勝任對專利輔助侵權行為的規(guī)制。如果不對專利輔助侵權進行專門立法而仍用共同侵權模式來處理的話,則勢必導致專利輔助侵權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的規(guī)制,不利于形成成熟的理論和制度。因此,我國必須在專利法中建立專門的專利輔助侵權制度,并在對這一復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加以詳細規(guī)定。
(二)利益平衡的啟示———應把握好專利輔助侵權制度保護的度
就本質(zhì)而言,專利輔助侵權制度是對專利保護范圍的一種擴張,即將專利的保護范圍從禁止他人制銷完整的專利產(chǎn)品擴張到禁止他人制銷作為專利產(chǎn)品主要組成部分的產(chǎn)品。但是,這一擴張不能是無限制的,否則將不當擴張專利壟斷權的范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就要求把握好專利輔助侵權制度保護的度。這一點從美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的發(fā)展歷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可以說,一部美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的歷史就是一部對專利輔助侵權制度保護的度的拿捏、衡量的歷史。
由此可見,專利輔助侵權制度的核心問題在于保護的度的把握,如果立法過程中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則勢必會導致專利權權利邊界的擴大,容易形成法外壟斷。
[54]在我國《專利法》的第三次修改中,國家知識產(chǎn)權局就不將間接侵權制度問題納入其中所作的解決也正是基于此方面的考慮,認為“在專利法中增加制止專利間接侵權行為的規(guī)定,實質(zhì)上是將對專利權的保護擴大到與專利技術相關,但其本身并未獲得專利權的保護的產(chǎn)品。因此,專利間接侵權問題已經(jīng)落入專利權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十分敏感的灰色區(qū)域,有關規(guī)則的制定和適用略有不當,就會損害公眾自由使用現(xiàn)有技術的權利。”
[55]因此,要構建、設計專利輔助侵權制度,必須特別重視并恰當解決這一問題。應通過制度的合理設計,使專利輔助侵權制度在為專利權人提供合理保護的同時又不至于逾越合理的限度。
(三)現(xiàn)實性立法技術的啟示———彈性立法
正如前文所述,專利輔助侵權制度構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度的把握,但從美國的相關制度歷史來看,這顯然是一個高難度的問題。為了尋找這個度的合理界限,美國的法官和立法者可謂絞盡腦汁,而至今尚無定論。百余年的爭論使美國的立法者開始意識到這條界線似乎永遠不可能劃定得清晰無爭。于是,他們開始在立法中采取一種更為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來處理這一問題。體現(xiàn)在立法技術上,便是美國1988年《專利法》所采取的彈性或模糊性的立法技術,即一方面提供一些明確的侵權構成要件,另一方面又授權法官們在一定范圍內(nèi)視個案具體情況判定是否構成輔助侵權。從而通過“剛柔并濟”的現(xiàn)實方法來最大程度地為專利輔助侵權的判定提供依據(jù)。 我國的專利輔助侵權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如何構建起合理的制度以達致專利權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將是一個核心難題。對此,可利用制度建設的后發(fā)優(yōu)勢,充分認識到輔助侵權保護的界限不可能在立法上厘定無爭的現(xiàn)實,從而借鑒美國的相關彈性立法技術。一方面,在立法上為專利輔助侵權的判定提供一些明確的要件標準,另一方面可有意識地預留一些彈性空間,授權法官視個案具體情況判定是否構成輔助侵權。這樣,既可以一定程度上為專利輔助侵權的判定提供可預見性標準,又可以保證個案審判中的合理彈性空間。這當為符合歷史經(jīng)驗的一種現(xiàn)實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