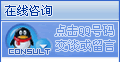近來,全國各地一、二線城市有計劃有步驟地集中出臺住房限購細則,落實中央關于房價調控的政策意圖,筆者稱之為“集束限購令”。其中“京版限購令”除了延續針對本市戶籍人口的一般性限購措施外,對非北京戶籍的人員購房的限制最為嚴厲,要求后者提供有效暫住證和連續5年(含)以上在北京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相關證明。縱觀各地政策調整之手段,“戶籍”再次成為殺手锏,在“限內”與“限外”之間刻畫出明顯的身份等級,刺激著人們對特權的聯想和對平等的期許。北京市房地產協會相關負責人稱“戶籍限購”是必要措施,而且政策效果不佳的話還要加大同一方向上的調控力度。限購令的表面政策目標是限制房價,但其涉嫌歧視危及了相關政策工具的合法性,鞏固并強化了特權城市和城市特權,在傳統的城鄉二元隔離之外增加了地區間隔離,不利于市場自由的擴展和公民認同的增進。
該項限購措施貌似“猛藥”,但卻并未擊中房價調控(尤其是一線特權城市)的要害,反而可能抵消法律平等和政治認同上業已取得的初步改革成果。該政策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值得商榷,限購令的功效與局限也需要反思。
戶籍歧視:
從城鄉結構到地區結構
京版限購令出臺不久,北京的王振宇律師即向國務院法制辦遞交審查建議書,指控北京市新版限購令涉嫌戶籍歧視。確實,限購令的政策要素包含“限內”和“限外”兩個方面,戶籍歧視至少體現在兩點:一是購房數量限制上“內”“外”不平等,戶籍人口可多購一套住房;二是對無住房的非戶籍人口提出了“5年”的嚴厲限制。王律師向國務院法制辦遞交審查建議的行為不太可能得到積極回應,因為北京市的限購令正是對國務院房價調控政策的落實,可能失之嚴厲,但政策目標是一致的。
以戶籍作為政策工具在共和國的成長歷史中并不罕見。在毛澤東時代,為維護林毅夫所謂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經濟戰略,城鄉二元結構獲得了體制化,“城市戶口”意味著充分的就業機會和福利保障,而“農村戶口”則意味著“禁錮”。改革開放通過對農民的土地經營放權和自治放權,實現了農村生產力的恢復和農民政治素質的提升,然而這些改革僅限于農村內部資源存量的結構性調整,尚未涉及城鄉平等問題。城市發展與農民工進城將城鄉平等問題正式“問題化”為我國政治和憲法上的嚴峻問題。“同票同權”、“同命同價”就代表了平等的時代呼聲。戶籍制度遭受批評的主要維度就是這樣的城鄉結構。
然而,限購令提醒我們,戶籍歧視不僅針對農村和農民,還在城市之間構筑起了新的樊籬。限購令的有效規制對象并非那些在城市沒有購房預期的農民工,而是相對于一線城市的那些二、三線城市的中產階層。以往的“購房入戶”畢竟還確定了一種相對明確的戶籍獲取條件,現在的限購令則從戶籍現狀出發限制購房。現在的關鍵已經不僅僅是你出生于城市還是農村,還包括你出生于哪個城市。在一線“特權城市”的決策者眼中,二、三線城市只是“更像”城市的農村罷了。以往我們憤慨于上海人歧視一切地方來的“鄉下人”,現在這種歧視則在房價調控的“政治正確”之下將既有的歧視予以擴充和強化。
限購令反映了城市群內部歧視的“地區結構”的凸顯,其背后是一種單向的“地區歧視主義”(地區保護主義可能是雙向的),這對于進行改革頂層設計的決策者們應具有警示意義。
特權城市:
高房價的真實因素之一
此次從中央到地方的“集束限購令”的直接原因是高房價。房價居高不下有著各種復雜的體制和市場原因,不同人士會根據自身偏向的原因提出不同的對策。筆者這里嘗試提出“特權城市”這一概念,作為分析高房價的因素之一。
所謂特權城市,指的是北京、上海、廣州之類的一線城市,它們通過歷史積淀和體制安排的方式獲取了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資源與成就,且通過戶籍福利的方式保持城市戶籍人口對發展成果的獨占。特權城市的高房價不完全是市場因素的結果,還有“超額福利”型特權的作用。比如高等教育領域,北京市名校林立,盡管是教育部直屬,是全國納稅人供養的事業單位,但對北京市戶籍子女的招生比例遠遠超過地方。著名憲法學者張千帆教授曾主持過高考地域歧視的研究課題,從理論和政策的角度深入剖析了相關的成因與狀況。這些一線城市的房價被“推高”,所反映的正是“購房入戶”的政策安排所承諾的“超額福利”。為了子女教育,地方各路諸侯,無論出身職業如何,均舉全家之力在北京購房入戶,他們所購買的絕不僅僅是單純的房地產,而是北京市的“超額福利”。因此,是受到體制保護的“超額福利”而非房地產本身的市場價值在支撐北京的高房價。從公平性上講,“購房入戶”畢竟有明確的市場標準,其政策正當性要超過目前的限購令。
特權城市的“超額福利”是高房價的真實因素,因此調控的方向就不是撕開法律平等的薄紗而重祭“戶籍”利器,而是反思這種“超額福利”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種“超額福利”的形成,在其歷史根據上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北京戶籍人口的貢獻,因此其成果也不能被北京戶籍人口獨占。毛澤東時代的財富積累模式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計劃體制,“戶籍”的意義早已超過了簡單的人口管理,而成為盛裝“特權”的巨大容器。改革開放以來,戶籍福利在社會平等化改革的進程中逐漸松動,但其中包含著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激烈博弈。限購令重新充實了“戶籍”的特權與福利內涵,與改革的分享邏輯之間存在緊張。可以預料,這種“毒性”極大的嚴厲調控不僅效果難以持久(因為這是治標不治本,最終還是要回到常態化的市場機制之中),而且會產生極大的副作用,比如再次動搖人們對市場自由、社會平等和政治認同的信心。
針對支撐高房價的“特權城市”因素,正確的政策思考方向應該是如何合理拆解那些“超額福利”。例如,北大清華這樣的全國性名校取消招生名額的地域歧視,實現平等競爭和公平招生,則窮舉家之力來京“購房入戶”的地方人士就會有更加理性的投資思考和生活安排。拆解“超額福利”不是要取消那些特權城市的所有福利,而是讓其恢復到法律和公眾可接受的合理水平,重點是拆解那些因歷史和體制慣例而不合理地歸屬于市民福利的相關內容。拆解允許一線城市保留部分只針對本市戶籍居民的合理項目。更宏觀地講,特權城市還根植于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國家在宏觀政策上應著眼于地區平衡發展的結構性設計,包括分散超大城市的功能、調控地區間發展的互補結構、在政策與法律層面不斷釋放公平機會并確立平等規則。
改革的政治理性:
“身份”與“契約”賽跑
戶籍是很重要的“身份”控制技術,一度成為改革的對象,但卻始終難以消解或轉型。英國著名歷史法學家梅因在其《古代法》一書中將法律發展過程概括為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身份”是特權的標志,來自傳統的政治概念和技術系統,以區分為前提;“契約”是自由的標志,來自古羅馬法,以平等為前提。梅因概括的法律史規律實際上也是政治社會史的規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自由的發展和國家政治法律結構的調整,其基本邏輯與發展主線正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進化線路,如不斷釋放身份束縛和特權空間。在改革30年“一起做大蛋糕”的過程中,由于大部分群體均能從發展中獲益,而且平等觀念和權利意識尚不發達,一些性質“嚴重”的歧視被“無知”地容忍了下來。但是,隨著改革轉向強調共享與公正的分配領域,改革初期的默契就被打破,特權群體希望借助一切政策機會和法律漏洞來鞏固自身利益。如何鞏固呢?第一步,確立具有“政治正確”性質的政策問題(如高房價),描述甚至夸大其嚴重程度;第二步,采用傳統的身份識別與控制技術(如戶籍)達到“排外”的目的(比如通過限購令推高房租價格,逼走在京“蟻族”,壓制京外人士來京預期);第三步,利用房市的價格剛性和周期反彈,不斷延續或重啟身份性調控。
我們看到,在改革新的三十年里,圍繞社會公正與個體自由的問題,很可能出現“身份”與“契約”賽跑的現象—這就是改革中的反復現象。政策調控往往沒有從從長效機制和公平政策的角度著手,這次的調控重新打開那只名為“戶籍”的“潘多拉之盒”,所遲滯和干擾的正是改革以來的“契約化”邏輯與進程。限購令所折射出來的政策設計者的“身份崇拜”表明其并沒有理解改革的“契約化”邏輯。
上面所論的“契約”尚為一種私人間的自由契約。還有一種更加重要的“契約”,即社會契約。以社會契約為基礎,我們通過憲法建構公民對國家的現代認同。這種政治認同是政治穩定的根本所在。限購令的政策效果可能會撕裂此類認同。現代政治必然是認同的政治,而不可能是管制的政治。特別是在全球化和高流動性的當代,如此嚴厲的、缺乏理性基礎和公正內涵的“身份”政治,其公眾認同度不可能高,而且有悖于改革以來的“契約化”共識。限購令可能不僅僅是房價調控,而且還是人口調控—重新“身份化”的政策出臺容易使人產生改革有倒退的聯想。
總之,限購令警醒我們,對房市的基于戶籍的調控在形式上違背憲法平等原則,在實質上偏離了支撐高房價的“特權城市”因素,將歧視擴延至地區之間,而且通過重新“身份化”來修正改革以來的“契約化”共識,抵制社會正義所包含的自由與公平的規范性訴求。更要命的是,針對這樣的“復辟”之舉和行政權力的強勢作為,我們竟然難以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從而彰顯出我國政治建設與法治建設對改革的共識原則及公民權利的捍衛能力之薄弱。如果此類政策斷斷續續、遮遮掩掩地得以長期化,改革其他領域取得的整合性與公平性成果將不斷地被抵消。政策的出路之一可以是回歸改革的共識理性,堅持“契約化”邏輯,弱化作為身份政治關鍵技術的戶籍控制,拆解特權城市的超額福利,側重保障性住房建設,宏觀設計地區間平衡發展規劃,真正以一種“包容性增長”的立場來設計、檢討與調整改革深水區的關鍵性政策。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