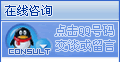���ߣ���܊
��(n��i)����Ҫ�����ڌ����`�����c��������������u�r�C(j��)�ƵĻ������J(r��n)�R���壬�҇��������W(xu��)�����`�������О�Ę�(g��u)��Ҫ��������������r��؟(z��)�εĚw؟(z��)ԭ�t�ȷ���a(ch��n)�����T���e�`�J(r��n)�R��������`������gesetzwidrig���nj��О鲻���Ϸ���Ҫ�������ġ����^�u�r��������@һ�u�r�C(j��)��������������Ҫ�l(f��)�]���������О��Ч���u�r֮������������������rechtswidrig�����鷨��؟(z��)�ΙC(j��)�Ƶ�����(d��ng)�Ի��A(ch��)��������������r��؟(z��)�Θ�(g��u)���аl(f��)�]���������О�ēp���Y(ji��)���Ƿ��������(d��ng)�Ե��u�r���ܣ������^�e���u�r�t���ڷ���؟(z��)�ΙC(j��)���еĚw؟(z��)Ҫ����������������ϣ������ڸ��Ե����x�}�j(lu��)�аl(f��)�]����ͬ�����ã�����һ���ķ�ʽ����B��������l(f��)��(li��n)ϵ��
�P(gu��n)�I�~���`�����������^ʧ��������r��؟(z��)�Θ�(g��u)��
һ��������}��������� ���`�����ֻ���������
���鷨�ɌW(xu��)�ϵ�Ҏ(gu��)�����Z�����`�����c���������ǃɂ����x�c���ܴ��ڲ�e��������s��������������c���h�ĸ�������������`����������˂�����Ϥ����ӽ��ճ�����߉�ķ��ɸ��һ����ָ�О��ڿ��^���c���ɵ�Ҫ���������������������x��(w��)���ֹ������`������[i]���������ϣ����`��������Ĺ�����Ҫ�w�F(xi��n)�������V�A�Ќ������О�Ч�����u�r���������О顰�`������ζ�����(n��i)�ݻ���ʽ�ڿ��^�ϲ����Ϸ��ɵ�Ҫ��������M(j��n)����(d��o)����Ч���ķ��J(r��n)���[ii]��������������t�Ǵ�ꑷ�ϵ�̷����֙�(qu��n)���c�����r�����Ϸ��(g��u)�ɡ��֙�(qu��n)؟(z��)�Θ�(g��u)�ɻ�����r��؟(z��)�Θ�(g��u)�ɵ���Ҫ�h(hu��n)��(ji��)֮һ���������(g��u)��Ҫ���������������ԡ��c����؟(z��)�ԡ������f�M(j��n)ʽ�ķ���؟(z��)�Θ�(g��u)�ɵ�����Ҫ�ء����С���������ָ�О�o����(d��ng)�����ֺ����˙�(qu��n)�棬���ڝM�㡰��(g��u)��Ҫ�����Ļ��A(ch��)�����������w������ǶȌ��О����ķ����u�r����[iii]
Ȼ�������ճ������Z���еġ��������c���`��������H�Z�x������ͬ���������S�������п��Ի��Qʹ�ã�[iv]�@������ʹ�˂�������������������ڷ����Z���еIJ�ͬ���x�c���ܣ��������l(f��)���P(gu��n)���h�����磬���������W(xu��)�о��I(l��ng)��������P(gu��n)���`�����c���������Ġ��h���ߌ������ͬ�ĬF(xi��n)��͕r�аl(f��)�����ƝԔ�����£�
���}һ�����`�����c���������Ļ��������`�������О���Ҫ���^�e��Ҫ�������
�P(gu��n)���`�������О�Ę�(g��u)��Ҫ�����҇��������W(xu��)��һ�N�V���������^�c(di��n)�J(r��n)�飺�`�������О�Ę�(g��u)��Ҫ�����H��M����^���`����������Ҏ(gu��)����������О������^��߀��횾����^�e�������[v]�W(xu��)����Փ��ԓ�^�c(di��n)�r���������b�����֙�(qu��n)�����̷��ϵ��`�����������W(xu��)�f���J(r��n)�������О��`���������������Σ�����������О��������^�����^�e�����О�����[vi]��֮�����������C(j��)�P(gu��n)�������О顰�ȷǹ����������Ҳ���^ʧ��������Ͳ���(g��u)�������`������[vii]�@�N�^�c(di��n)���Н��������֙�(qu��n)���ϡ��О��`�������������f������������ ���`���ԣ������ԣ����Д������M���`�������x��(w��)��������ֺ���(qu��n)���@һ�l��������������О��˵��^ʧ���Ҫ����[viii]���^�����Ї�����������W(xu��)���`�������О���J(r��n)�R���@Ȼ�ܵ���ԓ�W(xu��)�f��Ӱ�����
Ȼ�����֙�(qu��n)���W(xu��)�f���Q�ġ��`���������������(sh��)�H����ָ�����֙�(qu��n)؟(z��)�Θ�(g��u)��Ҫ���ġ�����������c�������W(xu��)������ġ��`���������О������ȫ�ǃɴa�¡������҇��W(xu��)�߲���ע�⡰�`�����c�����������Z�ϵą^(q��)�֣��@�������������W(xu��)���ڽ��b�W(xu��)�f�r���@�ɂ�����Ļ���[ix]�������֙�(qu��n)���ϵġ��О鲻�����f����ጡ��`���������О�Ę�(g��u)��Ҫ������M(j��n)���ó����`�������О������^�e��Ҫ����֮�Y(ji��)Փ����@���H��ȫ�����ˡ��`�����c���������ɷN��ȫ��ͬ���О��u�r�C(j��)��������������c�����V�A˾����(sh��)�`��Ҫ����㣡���(sh��)�H����������oՓ������������҇��������V�A��(sh��)�`��������`�������О���Д����һ�N���^��(bi��o)��(zh��n)�������o�迼���О���֮������^ʧ��ֻҪ�����О��ڿ��^���`���˾��w�ķ���Ҏ(gu��)������(g��u)���`����Ƿȱ�����^��֮����(d��ng)�ԡ��������[x]
���}���������О�Ŀ��^�`�����������ƶ��^�e������(j��)�
�c�������^�e�����`�������О阋(g��u)��Ҫ�����^�c(di��n)��ͬ������ЌW(xu��)���J(r��n)�飬�����О��`����һ�N���^�`��������@�N�`�����^�e�ı��F(xi��n)���������О���^�ϱ��F(xi��n)���`��������ȻԴ�����^�������^�e�������`���ı��|(zh��)��(y��ng)�J(r��n)�����^�e����`�������О�������ƶ��^�e������(j��)�� ���@�͂��y(t��ng)�����^�e����؟(z��)�εĸ�����һ�¡���������������r�����ϵġ��`�����w؟(z��)ԭ�t�䌍(sh��)�����^�e؟(z��)��ԭ�t����[xi]
�@�N�^�c(di��n)�c�����֙�(qu��n)؟(z��)���еġ��^ʧ���^�����C(j��)���H�����֮̎������ڌ��^ʧ���鲻����Ҫ���ġ��О鲻�����f����������О�Ŀ��^�`�������ƶ��^ʧ�ėl����������Ķ���(sh��)�F(xi��n)�^ʧ�J(r��n)���Ŀ��^������������֙�(qu��n)���ϡ��^ʧ���^�����C(j��)���еĿ��^�`����ָ�О��ˌ����^ע���x��(w��)Ҏ(gu��)�����`����[xii]��ô������������О�Ŀ��^�`����Ȼ�nj�ע���x��(w��)Ҏ(gu��)�����`���������������ǿ϶��������ô�����^�c(di��n)���Գ������������˾����(sh��)�`��������҂����l(f��)�F(xi��n)�S�������О��`�����o���J(r��n)���^�e�İ��������[xiii]��Ҋ������������е��`�������О鶼�������ƶ��О���֮�^�e����������О�Ŀ��^�`���c�^�e�������ڱ�Ȼ(li��n)ϵ����������r�����ϵġ��`�����w؟(z��)ԭ�t��ܵ�ͬ���^�e؟(z��)��ԭ�t����
���}���� ���`�����w؟(z��)ԭ�t�еġ��`�������Խ�ጞ顰���������������
������֪���҇������r�������m�á��`�����w؟(z��)ԭ�t����[xiv]�����������О顰�`������(bi��o)��(zh��n)�����J(r��n)����(sh��)�e�`������Խ��(qu��n)�����`����������ȣ���������r��؟(z��)�εĚw؟(z��)����(j��)�����Ȼ�������ԓ�w؟(z��)ԭ�t���J(r��n)��oՓ���ڌW(xu��)���ϻ��nj�(sh��)�`�^���ж����R���o���˷��������������`�����w؟(z��)ԭ�t�Ĵ���ʹ�Ç����r��؟(z��)�εij����o�����^�e��Ҫ�������ֻҪ��(d��o)���ֺ��Ĺ���(qu��n)���О顰�ڿ��^�Ͼ���ij�N�`����B(t��i)��������ɛQ��؟(z��)�εĚw�١��@��(d��o)����һ�N���εĿ��^�w؟(z��)�C(j��)���������[xv]����ԡ��О��`��֮���^��B(t��i)������w؟(z��)����(j��)�����(sh��)�H���ǻ����˷���؟(z��)�Θ�(g��u)���еġ����^�����ԡ��c�����^��؟(z��)�ԡ�Ҫ�أ��ڌW(xu��)�������y���ԈA���f�������[xvi]���顰���������ǣ���˾����(sh��)��(w��)�У�������Щ�M���`������������o���J(r��n)���^�e�Ĺ���(qu��n)���О��������ԡ����^�ϵ��`����B(t��i)������w؟(z��)����(j��)���M(j��n)�������r���ЛQ������(d��o)�����еIJ�������
���˻��⡰�`�����w؟(z��)ԭ�t��������Σ�C(j��)����������҇��ЌW(xu��)��������P(gu��n)�ڡ��`�����IJ�ͬ�������[xvii]�����J(r��n)�飬���`�����w؟(z��)ԭ�t�еġ��`������(y��ng)��(d��ng)������֙�(qu��n)���ϵġ������������ԡ��О鲻�����f����亭�x���ԡ��^ʧ�����顰�������ı�Ҫ�l�������Kʹ�á��`�����w؟(z��)ԭ�t�a(ch��n)���^ʧ؟(z��)��ԭ�t��Ч�������@�N��Q���}�ķ����c�҇��W(xu��)��ᘌ����}���mҪ���ķ��ɵ�ȡ��ͬ���w�F(xi��n)�˷���ጌW(xu��)���ǻ��c��ˇ������������}���������������ԡ������Ƿ���؟(z��)�ΙC(j��)����ᘌ��О�Ŀ��^�u�rҪ����������ԡ�������ȡ�����`��������w؟(z��)ԭ�t����δ����Փ��ʹ�����r��؟(z��)�Δ[Ó�����^�����ԡ��c�����^��؟(z��)�ԡ�֮��Ԫ��(g��u)�캬�첻��Ġ�B(t��i)������r�ң��ڮ�(d��ng)���҇��W(xu��)���������˾����(sh��)��(w��)�粢�����_�^(q��)�֡��������c���`���������������ԓ��ጷ������a(ch��n)���Č�(sh��)�HЧ�����˴��ɡ�
ᘌ��҇��������W(xu��)�о����P(gu��n)�ڡ��`�����c�������������ģ���J(r��n)�R�c���h�����ćLԇ�ķ����ό��@�ɂ�����ĺ��x��������u�r�C(j��)������������������U��������������ϸ��l(f��)�]�������c�����������ڴ˻��A(ch��)��ԇ�D����һЩ�e�`�J(r��n)�R�����ڰl(f��)�]��������Դ�������������
���� ���������c���`���������Ҏ(gu��)�����x�����u�r�C(j��)��
�h�Z���W(xu��)�е� ���������c���`����Դ�����ձ����W(xu��)�������ձ����W(xu��)�еġ��������c���`�������nj�������rechtswidrig�cgesetzwidrig�ķ��g�����������ʾ���`�����Ć��~��gesetzwidrig �����ʾ���������Ć��~��rechtswidrig��������������c���`�����ڝh�Z�ճ��Z���к��x�Ľ��ƅs����(d��o)���䷨�ɺ��x�Ļ������������鷨�ɸ���ġ��`�����c�������������⣬횏ġ������ĺ��x������������п�����������ڷ����x�W(xu��)�ϵIJ�ͬ���x��
�ڴ�ꑷ�ϵ���ҵ��Z������������������_�^(q��)�֞�ɷN������ʽ��������������Z�е�Jus��lex����������Z�е�droit��loit�������е�recht��gesetz�������������Z�е�diritto��legge��������������Z�е�derecho��ley��������ȵȡ�[xviii]�����քeָ��ͬ�ĺ��x���������һ���������е�lex�����loit�������gesetz��legge��ʾֱ�^���x�ϵij��ķ�Ҏ(gu��)�������w��Ҏ(gu��)����Ҏ(gu��)�t������������е�Jus��droit����recht�������diritto��ʾ�^�������^���Եķ�������w�ķ������rֵ���x�ϵķ�������ஔ(d��ng)��Ӣ�Z�е�justice��right�������С���ƽ���������x����������_���ĺ��x����[xix]�c֮������(y��ng)�����`�����c���������ĺ��x��ʬF(xi��n)���^��IJ������M(j��n)���γ��˃ɷN��ͬ���u�r�C(j��)�ơ�
��һ������(y��ng)�ڡ������ĵ�һ�Ӻ��x��lex��loit��gesetz�����legge�������`������ָ�����ķ�Ҏ(gu��)�������w��Ҏ(gu��)����Ҏ(gu��)�t���`�����[xx]�@��һ��ֱ�^��������ӽ��ճ�����߉�ķ��ɸ��ͨ���˂����f���`������ָ�О錦���w�ķ���Ҏ(gu��)�t���`�����ķ����u�r�C(j��)�ƽǶȿ���������`���ԡ���(sh��)�H��������(j��)��Ҏ(gu��)�����ض��О��������rֵ�������Ŀ��^�u�r��ֻҪ�О��c���w�ķ�Ҏ(gu��)�t���ֹ��������|���Ϳ������`�����u�r�����
����һ�N�����u�r�C(j��)��������`�����w�F(xi��n)�˷������x�{(di��o)����ʽ��Ҫ�����������ǿ��^���u�rҎ(gu��)���������`��������^�u�r��(bi��o)��(zh��n)�ķ�Ҏ(gu��)�����О���١��`������������Փ�О����ܷ�����Ҏ(gu��)�����Ƿ�����^�e������@�N���`���ԡ��u�r������Q�顰���^�`�����������[xxi]�����x���ڣ������`��ֻ����ζ�����^�ό�����Ҏ(gu��)�����`��������ˡ��`���ԡ��Д���(sh��)�H����ͨ�^���О�Ŀ��^�ġ����ڵı��F(xi��n)�c�Y(ji��)����Ҏ(gu��)�����Ķ��_���О���������_�����������������ķ�������֮�����������
�ڶ��������(y��ng)�ڡ������ĵڶ��Ӻ��x��Jus���droit��recht�����diritto��������������ָ�����^���Եķ���������w�ķ����rֵ���x�ϵķ������`����������P��ɭ���伃�ⷨ��Փ�Ќ������������������˜�(zh��n)�_���U�������P��ɭ�J(r��n)���������������О顱�Ľ綨��ڡ����w�������Ļ��A(ch��)�ϼ����Д࣬�������О顱�ǡ�����(j��)�����������D��횼��Ա��⡱���О����[xxii]�������������������О顱�Ƿ���؟(z��)���{(di��o)���C(j��)�Ƶ�ǰ��l���������ڡ������О顱�Ǐ����w������ĽǶȱ��x������u�r���О飬����(sh��)�H���ѽ�(j��ng)�|���������������̵ĘO�������ô���������ֻ�����Ʋ��@�N��(y��n)����Ҏ(gu��)���ֶΣ�����؟(z��)�Σ������{(di��o)������������@һ�J(r��n)�R�c�����T���еķ���؟(z��)����Փ��һ�¡����О�ġ������ԡ����������w�����������̣��Ƿ���؟(z��)���{(di��o)���C(j��)�Ʋ���ȱ�ٵ�ǰ��l���c����(d��ng)�Ի��A(ch��)������M���ڸ����T������������Բ������з���؟(z��)����ʽ��Ҫ������������ԡ������ԡ�����؟(z��)�ε�Ҫ���������������ʾ���Д�؟(z��)�γ������^���Пo�迼���������ԡ����������[xxiii]
���������u�r�C(j��)����Ҫ�w�F(xi��n)�ڵ����̷�����֙�(qu��n)���c�����r�����ϵķ���؟(z��)�Θ�(g��u)�������������������^�c(di��n)����������������鷨��؟(z��)�Θ�(g��u)�ɵ�Ҫ��֮һ�������ָ�О顰�o����(d��ng)���ɮa(ch��n)�����Ɖķ�����ĺ��������[xxiv]�������ԡ��Д������О�M�㘋(g��u)��Ҫ���Ļ��A(ch��)�ϣ������О�Y(ji��)����(d��o)�µę�(qu��n)��p���Ƿ�������w���������x�ϵġ�������s���ɡ�����������(d��ng)���l(w��i)��������o�����U���������О顢��ʹ��(qu��n)�ȣ�������߂䡰������s���ɡ�����(g��u)�ɲ��������ض����О�ֻ���ڿ��^�Ͼ߂䡰�����ԡ��������M(j��n)�롰��؟(z��)�ԡ�������Д�����������^�����ԡ��c�����^��؟(z��)�ԡ���(g��u)���˷���؟(z��)���u�r�C(j��)�Ƶăɴ���ĭh(hu��n)��(ji��)���[xxv]˾����(sh��)��(w��)�е������^�c(di��n)���������ԡ���λ�ڿ����О��ڡ��Y(ji��)���ϡ���(d��o)�µ��ֺ��Ƿ����w�����������������@�N�W(xu��)�f������Q�顰�Y(ji��)�������� �f��Erfolgsunrecht����[xxvi]
�����Y(ji��)���������f��(g��u)������(zh��n)���ǡ��О鲻�����f��Handlungsunrecht�������[xxvii]ԓ�W(xu��)�f�J(r��n)�飬�Д���Բ��H횿����О�ĽY(ji��)�����������������P(gu��n)ע�О鱾������������ǹ����ֺ����˙�(qu��n)����������О鲻���Եij�������О��˵��^ʧ���Ҫ�������^ʧ���Д��t���á��`���ԡ��u�r�C(j��)�ƣ�ֻҪ�О����ڿ��^���`���˷������еġ�ע���x��(w��)Ҏ(gu��)���������ƶ��^ʧ����������^ʧ�Ŀ��^��������֮��������О����ѱM����Ҫע���x��(w��)�r����ʹ���О�����ֺ����˙�(qu��n)��Ŀ��^����������Ҳ���ܱ��J(r��n)�阋(g��u)���`������������О鲻�����f��ȱ�ٺ�����ע�����Ӟ顰����������ĽM�ɲ��֣�����������ζ���^ʧ�Ĵ�������
�C�Ͽ�֪�������鷨�ɸ���ġ��`�����c����������Ҏ(gu��)�����x����u�r�C(j��)�ƾ��������^���e�����҂������ճ������Z���ĽǶȌ��������뮔(d��ng)Ȼ��������������ڲ�ͬ�ķ��I(l��ng)��߂���Ե����x�}�j(lu��)����Ķ��l(f��)�]��ͬ�Ĺ��ܡ��@Ҳ���҂��J(r��n)�R�������ġ��`�����c������������Ĺ����ṩ���J(r��n)֪������
������ ���`�����c�����������������ϵĹ���
��һ�� ���`���ԡ��Дࣺ�����О�Ч���Ŀ��^�u�r�C(j��)��
����������������`�������l(f��)�]�������О�Ч���u�r����Դ���ڡ�����������ԭ�t��Ҫ����������@һԭ�t�Ƿ������x�{(di��o)����ʽ���������ϵ��w�F(xi��n)�����������Ҏ(gu��)��������^���u�r��(bi��o)��(zh��n)�������(sh��)�F(xi��n)�������О�Ч�����u�r�cҎ(gu��)�������Ķ���K�l(f��)�]�Է��ɾ������������y(t��ng)��������������Ĺ��ܡ��@�N�{(di��o)����ʽ�����ڄP��ɭ�ķ�Ҏ(gu��)���wϵ��Փ�е��Խ�������
�P��ɭ�J(r��n)�飬�ڷ���Ҏ(gu��)���wϵ���������˻��A(ch��)Ҏ(gu��)����Grundnorm��֮������κ�Ҏ(gu��)�������з����m�úͷ��Ą�(chu��ng)��֮�p�ع��ܡ������О���˾����m�÷��ɵġ���(zh��)�С������������ͬ�rҲ�܄�(chu��ng)����w�ę�(qu��n)���x��(w��)�P(gu��n)ϵ����ɞ���w������ĜYԴ�����������������О�Ҳ���ڷ���Ҏ(gu��)���wϵ�е�һ���h(hu��n)��(ji��)������С����eҎ(gu��)�����Č��ԡ�[xxviii]�ڡ�����������ԭ�t֮��������Ɍ������О���{(di��o)����(sh��)�H�Ͼ����ԡ���Ҏ(gu��)����������(j��)�����顰�ͼ�Ҏ(gu��)�����������О��Ҏ(gu��)�������佹�c(di��n)�����Д������О��Ƿ��ڙ�(qu��n)�ޡ���ʽ�c��(n��i)�����`������λ���YԴ���ľ��wҪ�����һ�������О鼰������(chu��ng)�O(sh��)�ľ��w������֮���ԺϷ�����������ɘ�(g��u)�ɷ�����һ�h(hu��n)����һ��Ҏ(gu��)������(chu��ng)�O(sh��)�����ڙ�(qu��n)��������ʽ�c��(n��i)���Ϸ�������wҪ������[xxix]���������������О�ġ��`���ԡ����Ϸ��ԣ��Д���������(j��)��λ��Ҏ(gu��)�������ľ��w������������^���u�r��ֻҪ�����О��c���w����λ��Ҏ(gu��)������|�����dz�ֱ�^�������`�����u�r���@��һ�N���ڵ�����������^��Ч���u�r�C(j��)�ơ���һ�������О阋(g��u)�ɡ��`�������������������Ч���ϵ�覴����������ԓ�����О�����(chu��ng)�O(sh��)�ľ��w�����������w�������Ҫ������Ķ���(d��o)�������О鱻���N��׃����_�J(r��n)�oЧ�����
�@�N�u�r�C(j��)�Ʋ����漰�О��˵����^�^�e���ڷ���������������u�r�C(j��)���Ќ��О����^�e��̽��֮��Ҫ�������ڴ_������؟(z��)�εĚw�٣��^�e��ζ�����О��˾���ij�N�ڵ��x�ϑ�(y��ng)�ܷ��y��������B(t��i)������������ǡ�������־֧���µ��О�IJ���ԭ��ԡ����[xxx]���^�e����w؟(z��)����(j��)�ǬF(xi��n)������؟(z��)����Փ�����Ҫ������֮һ�����������О�ġ��`���ԡ��Дಢ�����ڴ_������؟(z��)�εĚw�����������ֻ�漰�О�Ч�����u�r�������ͬ����������`�������О飨Ч���ϵ�覴ã�Ҳ������Ȼ��ζ���О������^�^�e�Ĵ������
������ �������ԡ��Дࣺ�����О�p�����������(d��ng)���u�r�C(j��)��
���鷨��؟(z��)�ΙC(j��)�Ƶ�ǰ��l���c����(d��ng)�Ի��A(ch��)�����������ԡ����������ϵĹ�����Ҫ�w�F(xi��n)�������r��؟(z��)�Θ�(g��u)��֮���������������^�������UጵĮ�(d��ng)���ձ��Լ��҇��_���^(q��)�ć����r�������ձ���������_���ć����r����Ҏ(gu��)�����ԡ�������^ʧ���c�������ֺ��������Ҫ�ص������r��؟(z��)�Θ�(g��u)���������ڲ�ͬ�ČW(xu��)�f��ጌW(xu��)�M(j��n)·�������r��؟(z��)�Θ�(g��u)���еġ������ԡ��Д��ͨ�^��N��ʽ�w�F(xi��n)�����������
��һ���������(j��)��˾����(sh��)�`��̎������(d��o)��λ�ġ��Y(ji��)���������f��������r��؟(z��)�Θ�(g��u)�ɰ������A�ӡ��f�M(j��n)ʽ��߉�Y(ji��)��(g��u)��չ�_��������(g��u)��Ҫ�����������Д����؟(z��)���Дࡱ��������ڂ������������ijһ�����О��ֺ����˙�(qu��n)�������Ϙ�(g��u)��Ҫ��������M(j��n)�롰�����ԡ��Д��A�Ρ�������ԓ�����О���ɵę�(qu��n)���ֺ��Y(ji��)���Ƿ�������w���������x�ϵġ�������s���ɡ�������(d��ng)���l(w��i)��������o�����U���������(w��)�ȣ��������������߂䡰������s���ɡ��������ԓ�p����(qu��n)��֮�Y(ji��)������(g��u)�ɡ����������Ķ��M(j��n)�롰��؟(z��)�ԡ��Д��A��������������О��ˣ������C(j��)�P(gu��n)���乤���ˆT�����^���Ƿ���ڹ�����^ʧ������������О�ͬ�r�M�㡰���^�����ԡ��c�����^��؟(z��)�ԡ��ɂ��l�����t�����r��؟(z��)�γ�������
����������(j��)���О鲻�����f����(g��u)�����r��؟(z��)�Θ�(g��u)�ɣ������^ʧ���J(r��n)���ǡ��������ı�Ҫ�l�����[xxxi]�����О�ēp���Y(ji��)���Ƿ�(g��u)�ɡ�������ȡ�Q���О����Ƿ����^ʧ�Ĵ�����������M(j��n)�С������ԡ��Д��r�ѽ�(j��ng)���О��˵��^ʧ���]�ڃ�(n��i)���漰�w؟(z��)Ҫ�صĿ�������������@��һ���̶��ϸ�׃�˷���؟(z��)���С����^�����ԡ��c�����^��؟(z��)�ԡ�֮����Ҫ��չ�_������c��(g��u)�죬���oՓ�����ķN���������W(xu��)�f�����ڴ����(sh��)�����r������̎���Y(ji��)�����o��e��
�����������ɷN�������֙�(qu��n)؟(z��)�Ξ鷶ʽ�������r��؟(z��)�Θ�(g��u)�ɵĽ�������ˏV���Ġ��h��������S���W(xu��)���J(r��n)�����������r�����ķ������|(zh��)�ٹ�����������ڹ����ϣ��������ڃ�(y��u)Խ��λ����������������ֺ����˙�(qu��n)���������О����еõ������ڙ�(qu��n)�ߣ��繫�����գ�����˲����հ�����Փ����ʹ����(qu��n)���ֺ���(qu��n)�����О�ҕ�顰�����������������r��؟(z��)�Θ�(g��u)�ɵġ����������(y��ng)��(d��ng)��ጞ������V�A���x�ϵġ��`������������������Ҫ�c(di��n)���ڌ�(d��o)��(qu��n)��p���������О��Ƿ��`���˷�Ҏ(gu��)�������`�������О���ə�(qu��n)���p�����m�Ç����r��؟(z��)�ε�ǰ��l����[xxxii]�����@�N˼·������ԡ��`���ԡ�ȡ���������ԡ�����M(j��n)������(g��u)���c���y(t��ng)��Փ������ͬ�ć����r��؟(z��)�Θ�(g��u)�ɣ����ijһ�����О錧(d��o)�������˙�(qu��n)��p�������t����ԓ�О��Ƿ��ڿ��^���`���˾��w�ķ�Ҏ(gu��)�����`�����Дࣩ��������(g��u)�ɡ��`�������t�M(j��n)����؟(z��)���Дࣨ�����О����Ƿ���ڹ�����^ʧ�������ڴ�˼·֮��������������r��؟(z��)�Θ�(g��u)�ɰ����� ������(qu��n)���О顱��������p����������� ������P(gu��n)ϵ�������`���ԡ��c����؟(z��)�ԣ�������^ʧ�����״�Ҫ�������
Ȼ��������ķ���؟(z��)�Θ�(g��u)�ɵĺ���Ҫ�ؽǶȷ�������M�ܡ��`�����c�����������u�r�C(j��)�ƴ��ڲ�e����������`���ԡ��Д��������r��؟(z��)�Θ�(g��u)������Ȼ�l(f��)�]���������О錧(d��o)�µę�(qu��n)���ֺ����Ƿ��������(d��ng)����������Ƿ�����w�����������̡��������������ԡ��u�r֮���ܡ���������A�ӵ������r��؟(z��)�Θ�(g��u)����������顰�����ԡ��Д�����(j��)�ġ�������s���ɡ�������(d��ng)���l(w��i)����o�����U�c������(w��)�ȣ�������䌍(sh��)����������(zh��)���ˆT�ھo����r��(sh��)ʩ�ġ����r��(qi��ng)�ơ���ʩ��������^�����r��(qi��ng)�ơ����������ָ�����C(j��)�P(gu��n)���ڬF(xi��n)�r�l(f��)��֮�o��Σ����ᘌ��ض����������˵���������О��ؔ�a(ch��n)��ȡ�ļs����̎���Եď�(qi��ng)���О��������Ŀ���Ǟ����ھo������б��o(h��)������������˙�(qu��n)�治���ֺ�������������ֹ����p���İl(f��)�������[xxxiii]�������ϵġ����r��(qi��ng)�ơ���ʩ�ڰl(f��)�ӗl������Ҏ(gu��)��Ŀ�ķ����c����(d��ng)���l(w��i)���o�����U��ȫһ���������Կ���������(d��ng)���l(w��i)����o�����U���������ϵı��F(xi��n)��ʽ���������r��(qi��ng)�ơ��@Ȼ����������(zh��)���ˆT�Ϸ���������(w��)���О��������ˣ������r��؟(z��)�Θ�(g��u)���Ќ��ڡ�������s���ɡ��Ŀ��������ϾͿ����D(zhu��n)�Q�錦�����О��Ƿ���ںϷ�������(w��)�О���Д�����ڡ�����������ԭ�t֮��������һ�������О��Ƿ���ںϷ�������(w��)�О���Д࣬��Ȼ������(j��)���w����λ��Ҏ(gu��)������������(qu��n)��������(n��i)�ݡ���ʽ�c�����Ҫ���Ƿ��ڿ��^�Ϸ��Ϸ���Ҫ��ġ��`���ԡ����Ϸ��ԣ��Д��������������������О���ɵę�(qu��n)���p������Ƿ���С������ԡ��Ŀ������ͱ��D(zhu��n)�Q���ˌ�ԓ�����О�ġ��`���ԡ����Ϸ��ԣ��Д��ˡ�
�@һ�Y(ji��)Փ��ʾ�������r��؟(z��)�Θ�(g��u)���С������ԡ��u�r�c���`���ԡ��u�r��ͬ�|(zh��)�ԣ���Ȼ�������О���ɵę�(qu��n)���p������Ƿ���С������ԡ����Д࣬�ڷ��ɼ��g(sh��)�Ͽ����D(zhu��n)�Q�錦ԓ�����О��Ƿ�Ϸ��ġ��`���ԡ� �Д������ô����҂�Ҳ�����J(r��n)�飬���`���ԡ�ͨ�^����ə�(qu��n)���p���������О��ڿ��^���`����λ��Ҏ(gu��)�������Д����������(sh��)�H�ϰl(f��)�]���������ԡ��u�r�Ĺ����������
�ɴ˿�Ҋ���������r���������|(zh��)��λ�ڹ�������������������V�A���x�ϵġ��`����ȡ�����y(t��ng)�֙�(qu��n)���ϵġ�������������(g��u)�������r��؟(z��)�Θ�(g��u)�ɣ��c���A�ӵ������r��؟(z��)�Θ�(g��u)��֮�g���o���|(zh��)��ͬ������߶��@ʾ�������^�����ԡ��c�����^��؟(z��)�ԡ��ķ���؟(z��)�ζ�Ԫ���Ę�(g��u)�������
����������Y(ji��)Փ������һЩ�e�`�J(r��n)�R
���ĵķ��������ˡ��`�����c���������ɷN��ͬ�ķ����u�r�C(j��)�ơ��������������������ڸ��Ե����x�}�j(lu��)�аl(f��)�]����ͬ�Ĺ�������ͬ�r����һ���ķ�ʽ����B���������P(gu��n)(li��n)��������@�ɷN�u�r�C(j��)�ƵĻ������J(r��n)�R����������������҇��������W(xu��)��ijЩ�e�`�J(r��n)�R�ĸ������Y�Y(ji��)�����ڡ�
���ȣ����`�������О�����^�e��Ҫ�������^�c(di��n)֮�����e�`����Դ���ڌ����`�����c���������Ļ�����������e�`���ԡ��О鲻���f��������`�������О�Ę�(g��u)��Ҫ����������M(j��n)����(d��o)������؟(z��)�ΙC(j��)���еĚw؟(z��)Ҫ�أ����^�e���Дࣩ����(d��ng)?sh��)����뵽���������О�Ч���u�r�C(j��)�Ƶġ��`���ԡ��Д�֮�С���(sh��)�H�ϣ��@�N�^�c(di��n)���H�c�����������О���Փ������������������˾����(sh��)�`���ཛ(j��ng)������������ͨ�f�J(r��n)�����������О鷨��Ч���Įa(ch��n)������Ҫȡ�Q�ڱ�ʾ���ⲿ���О���^�ΑB(t��i)�����������О�ֻҪ�ڿ��^�ό��ض������˵ę�(qu��n)��a(ch��n)����ֱ��Ӱ푻���������������ҕ��l(f��)������Ч������[xxxiv]���������О鷨��Ч���Įa(ch��n)��������ه�О��˵����^��˼����ô���䷨��Ч�����`�����Д�����������o��̽���О��˵����^������B(t��i)������������҇��_���W(xu��)�������������ʹ�ǡ�����ʧ��֮����(w��)�T�ڟo���R�����e�y��B(t��i)����֮����̎�����������ԓ̎�ֿ��^���Ѿ߂�Ϸ�֮Ҫ��������Ч�����������Ӱ푡������[xxxv]�������V�A˾����(sh��)�`�������������`�������l(f��)�]�Č������О�Ч�����u�r������Ҫ�w�F(xi��n)�ڡ���ͻ����`�������О顱��Ϸ��Ԍ����ṩ�Д����(zh��n)���^��֮�������M�ܸ������ƌ��`�������О���w��͵İ��ճʬF(xi��n)�������ۻ����y�IJ�e�����ķ����m��߉Ҫ�صĽǶ��M(j��n)�Кw�{�c������������Ȼ���Ԍ����^��Ҏ(gu��)���ر����顰���w�`���������������Խ��(qu��n)���������E����(qu��n)�������������`������������(n��i)���`���������������`�����������������(j��)�`�����c����(sh��)����(j��)�`�����ȷ��������[xxxvi]����Ϸ��Ԍ������(zh��n)���`�������О���w����������m���^���о���ѭ���^��(bi��o)��(zh��n)�������������(j��)�����������О�Ŀ��^���F(xi��n)�����`���c����Д�������δ�漰�О������^�^�e���u�r�����ʹ�����О������^�әC(j��)�`����Ҫ�صġ������E����(qu��n)�����o�迼���О������^���Ƿ�����^�e�����(sh��)�H�ϣ��Д�ijһ�����О��Ƿ�(g��u)�ɡ������E����(qu��n)���Ǹ���(j��)�О���^����������ڵı��F(xi��n)�ƶ��Ƿ���ڡ��`������Ŀ�ġ��������]�����P(gu��n)�����ء����`������������ڌ�(d��o)���`����ԭ���Ƿ�����О��˵Ĺ�����^ʧ�t��������������������҇��W(xu��)�����ԣ������О阋(g��u)�ɡ������E����(qu��n)����������H���������О��ː�����ʹ������(qu��n)���`����������������������О��˳��������әC(j��)����(d��o)���О�Ŀ���c����Ŀ�IJ�һ�µ����Ρ������О������^���Ƿ�����^�e��������nj������О��M(j��n)�кϷ��Ԍ���r��횿��������ء�[xxxvii]
��Σ��������О���^�`�������ƶ��^�e������(j��)��������M(j��n)�������`�����w؟(z��)ԭ�t��ͬ���^�e؟(z��)��ԭ�t�^�c(di��n)���e�`֮̎���ڡ��������О鲻�����f�еġ��^ʧ���^����������һ�N���ε�����������������������������^ʧ���^�����J(r��n)���C(j��)���е��^ʧ�ƶ��H���ڌ���ע���x��(w��)Ҏ(gu��)�������`�����������е��О顰�`����B(t��i)�����������J(r��n)���^ʧ������(j��)��������`�������О���ΑB(t��i)ʮ�֏�(f��)�s����@Ȼ�o�������е��`�������О鶼��ȫ�w�Y(ji��)�ڌ��������ϡ�ע���x��(w��)Ҏ(gu��)�������`����������յ��������ϵ�ͨ�f�����`�������О����`���ķ����x��(w��)���Է֞�ɷN��ͣ�ᘌ����ҵġ�һ���Թ����x��(w��)���cᘌ��ض��˵ġ������˵ı��o(h��)�x��(w��)����������Ҏ(gu��)�����P(gu��n)�ڡ������˱��o(h��)�x��(w��)���ėl�(sh��)�H�Ϟ������C(j��)�P(gu��n)�O(sh��)����ᘌ��ض��˵�ע���x��(w��)����ע���x��(w��)�Ŀ��^�������������`�����ƶ��^ʧ�Ĵ��ڡ�����һ���Թ����x��(w��)������ֱ��ָ�������C(j��)�P(gu��n)�c�ض���֮�g���P(gu��n)ϵ�����@�N�x��(w��)���`�����������ƶ��^�e�Ĵ��ڡ�[xxxviii]��ˣ��������е��`�������О鶼�������ƶ��^�e�Ĵ�������������`�����w؟(z��)ԭ�t���o����ͬ���^�e؟(z��)��ԭ�t��
�������҇��W(xu��)�ߞ�˷����`�����w؟(z��)ԭ�t������������ķ��������ԡ��О鲻��������ጡ��`���������Kʹ�á��`�����w؟(z��)ԭ�t�a(ch��n)���^ʧ؟(z��)��ԭ�t��Ч�����������ص��� ���`�����w؟(z��)ԭ�t�����R�����֡�������؟(z��)�Θ�(g��u)���С����^�����ԡ�����������^��؟(z��)�ԡ���Ԫ����Ҫ�صĻ������`���w؟(z��)ԭ�t�ĸ������Y�Y(ji��)�����ڡ��w؟(z��)ԭ�t���ڷ���؟(z��)�Θ�(g��u)���д_��؟(z��)�Κw�ٵ�Ҫ���������^��؟(z��)�ԡ����������`�����t�nj��О�Ŀ��^�u�r�C(j��)�ƣ��������r��؟(z��)���п������顰���^�����ԡ�Ҫ������������@����(li��n)ϵ��һ����(chu��ng)�O(sh��)���^�ġ��`�����w؟(z��)ԭ�t����ӳ�������ߌ�����؟(z��)����Փ���J(r��n)�R�����`�^(q��)���@һ�e�`�ĸ�Դ�����ڌ����`�����c������������Ļ��������ڽ��b����������(j��ng)���^��������������ձ�������_�������r��؟(z��)�Θ�(g��u)���еġ����������ε�����������V�A���x�ϵġ��`����������ó��ձ����_�������r��؟(z��)�Θ�(g��u)��Ҳ���á��`�����w؟(z��)ԭ�t֮�Y(ji��)Փ���������֧���҇�����ģʽ֮���C��[xxxix]�����J(r��n)��������Q�@һ���}�ĸ�����·���S��������������҇��ć����r��؟(z��)�Θ�(g��u)����Փ��������_�����^�����ԡ��c�����^��؟(z��)�ԡ���Ԫ��(g��u)��Ļ��A(ch��)�ϣ��_���^�e�w؟(z��)ԭ�t�C(j��)�����ʹ���`��������ؚw������r��؟(z��)�Θ�(g��u)���еđ�(y��ng)�е�λ�����
--------------------------------------------------------------------------------
��*����ϵ����x�������ֵĽ������܌W(xu��)����ƌW(xu��)�о��ش��n�}���P(gu��n)�Ŀ���҇��ط����ƽ��O(sh��)��Փ�c��(sh��)�`�о���֮�A���Գɹ���
עጣ�
[i] ��Ҋꐾ��x����Ҏ(gu��)�����A(ch��)�ϵĺϷ��^�����Փ�`���������c�Ϸ����P(gu��n)ϵ�����������Փ����2006���2�����
[ii]��Ҋ����������˾������Ļ���(zh��n)����̽�������V�A�IJ��м��g(sh��)��������ɳ�����2005��棬��250��251��������
[iii]��Ҋ��d�����������w�̷��W(xu��)�������̄�(w��)ӡ���^2001����418���������b�������֙�(qu��n)�О鷨������һ�ԣ������Ї�������W(xu��)������2001������������88퓡���232������
[iv]�ճ������Z���еġ��`����ͨ��������顰�`�����ɡ���������������t����顰���ط������ط��������ߺ��x�����ڸ����^(q��)�e�����(d��ng)�҂�ָ�Qijһ�О��ǡ��`���О顱�r�����Q��顰�����О顱��δ�L������������Ҋ�W(w��ng)�j(lu��)�~�䡰�h�䡱��http://www.zdic.net/cd/ci/4/ZdicE4ZdicB8Zdic8D28528.htm�������2010��10��21���L����
[v] ��Ҋ�S������Ƥ���f(xi��)�������Ї��������W(xu��)�о��C���������ɳ�����1991��������516���������������������������W(xu��)��������ɳ�����2002����431퓵ȡ�
[vi] ��Ҋ���ɗ���������؟(z��)��Փ����������Ї�������W(xu��)������1998���������15-16�����
[vii]��Ҋǰ���S��¡�Ƥ���f(xi��)���������516퓡�
[viii]��Ҋǰ�������b�����������230퓡�
[ix]�����`�����������������������Ļ���ͬ��Ҳ�l(f��)�����֙�(qu��n)�������̷��о��I(l��ng)����������҇��W(xu��)�������·��(g��u)�ɡ��֙�(qu��n)؟(z��)�Θ�(g��u)�ɵ��о��I(l��ng)�����������ע�⡰�������c���`�������Z�ϵą^(q��)�֣��á��`����ָ�Q���������ѳ�˾��Ҋ�T֮����������ֽ�����ָ������������̷��W(xu��)�о��У�����(n��i)�W(xu��)�߽�(j��ng)�����h�Z�еġ��`���ԡ��c��ꑷ�ϵ�̷���Փ�еġ��`���ԡ��������ԣ����ã���Ҋ��������������`�����J(r��n)�R�����������W(xu��)�����������2006��������5퓣�������������֙�(qu��n)���I(l��ng)�����ijЩ�W(xu��)�������֙�(qu��n)؟(z��)�Θ�(g��u)���еġ������ԡ��Д��`����ض��О����(sh��)�Ƿ��`�����w����Ҏ(gu��)�t�ġ��`���ԡ��Д���������Ҋ����������Փ�֙�(qu��n)���İl(f��)չ������d�ڡ��Ї����W(xu��)��(chu��ng)�¾W(w��ng)���v�����͙�Ŀ����http://www.lawinnovation.com/html/jzjz/063511.shtml���2010��4��15���L��������
[x]��Ҋ�~���ޣ��������r����֮��Փ�c��(sh��)��(w��)���������Ԫ�ճ�����2009����145퓣���������������V�A�����P(gu��n)����̎��֮�о�������_��˾���ܿ���1989����������43������
[xi] ��Ҋ��С�������������r�����Ɇ��}�о��������������W(xu��)������2005������������126퓡�
[xii] ��See Draft Restatement(Third ) of the law ,Torts: Liability for Physical Harm, Tent. Draft No. 1(March 28 2001),��1, comments a, d..
[xiii]���磬��(d��ng)���˴�ͨ��Ӌ����(w��)��������ʽ����ȫ�Ϸ���̓�ٳ��Y�C���������C(j��)�P(gu��n)��Ո��˾ע�Ե�ӛ�������C(j��)�P(gu��n)�ڱM�˷����Č����x��(w��)��δ�l(f��)�F(xi��n)�����������C�l(f��)�I�I(y��)�S��������º�������V�A��������Ժ�J(r��n)��ԓ�I�I(y��)�S���`����������Ҫ�C��(j��)�ij��Y�C��ϵ���죩���ЛQ���N�������������I�I(y��)�S���`�����ƶ������C(j��)�P(gu��n)�����^�e����������C(j��)�P(gu��n)�ڌ����^�����ѽ�(j��ng)�����˷����Č����x��(w��)�����
[xiv] 2010����ӆ�ġ������r��������2�l�hȥ�ˡ��`����֮Ҏ(gu��)�����@��ζ�����`���������LJ����r��؟(z��)��Ψһ�Ěw؟(z��)ԭ�t����ijЩ�����¿��m�á��Y(ji��)��؟(z��)�Ρ��w؟(z��)���������`�����w؟(z��)ԭ�t�Ԍ��������r�����������r����Ҫ�Ěw؟(z��)ԭ�t��
[xv]��Ҋ������������Ї��������W(xu��)ԭ�������Ї�������W(xu��)������2002��棬��256��������
[xvi] ��Ҋ��Ҋ��܊ ��������������؟(z��)�θ������ʽ��(g��u)�졷����������W(xu��)�о���2010���4�������
[xvii]��Ҋ�ܝh�A����Փ�����r��?sh��)��^ʧ؟(z��)��ԭ�t���������W(xu��)�о���1996���3�ڣ������i���������r���`���w؟(z��)ԭ�t�ĺ�����λ����������������W(xu��)�о���2008���1�ڣ�ǰ����܊�����������������
[xviii] ��Ҋ�����@������������W(xu��)��������ߵȽ��������������������W(xu��)������1999����������43�����
[xix] ��Ҋǰ������֕�����6��������
[xx]��Ҋǰ������֕��������6����
[xxi] ��Ҋ���������������������W(xu��)�����ߵȽ���������2004������������317���������R�˲��������^�̷�ԭ����������̷��W(xu��)��Փ���������h��W(xu��)������2002���������311퓡�
[xxii]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111;���W���P��ɭ���������ⷨ��Փ����������������g����Ї����Ƴ�����2008��棬��57������
[xxiii]��Ҋ�������������p���r����ԭ�������Ї�������W(xu��)������2010���������59�����
[xxiv] B.S. Markesinis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 Volume �� The Law of Tort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3rd .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68.
[xxv] ��Ҋ����܊���������ϵ��`������Փ�о��������F(xi��n)�����W(xu��)��2007���1�ڡ�
[xxvi] ��Ҋǰ�������b������229퓡�
[xxvii] See B.S. Markesinis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 Volume �� The Law of Tort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 3rd .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97. p70.
[xxviii] �ڄP��ɭ������Ҏ(gu��)����ָijЩ�¡���(y��ng)��(d��ng)����λ�(y��ng)��(d��ng)���l(f��)���������߀��(qi��ng)�{(di��o)ij�ˡ���(y��ng)��(d��ng)�����ض���ʽ�О顣�������Ҏ(gu��)�����H�����������������߀���S�������ڙ�(qu��n)�����x�{�����У� 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p.4��5.���������О�����һ�N����(qu��n)�����������Є�(chu��ng)�O(sh��)�����P(gu��n)ϵ�Ĺ����������������(chu��ng)�O(sh��)�ķ����P(gu��n)ϵ������Ҫ���ض��ˡ���(y��ng)��(d��ng)����ij�N��ʽ�О�֮���x�������������О������Ҏ(gu��)���Č���������������О�ϵᘌ��ض��˵ġ����eҎ(gu��)������������Ǿ����ձ��m�����ġ�һ��Ҏ(gu��)�������
[xxix] 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p233��236..
[xxx] ��Ҋ��܊��������؟(z��)�ε��pԪ�rֵ��(g��u)�졷�����㽭�W(xu��)����2005���1�������
[xxxi] ���О鲻���f����ǰ��l���Dž^(q��)�ֹ����c�^ʧ���֙�(qu��n)�О飬���ڹ����nj��������������ɵ��������@���`�����������ֻҪ��(d��o)��(qu��n)���ֺ��Ϳ��J(r��n)���������������О鲻���f����Ҫּ���ڌ��^ʧ�ַ���(qu��n)���О���J(r��n)������ǰ������܊��
[xxxii] ��Ҋǰ���~���ޕ������142퓡�
[xxxiii]��Ҋǰ�������������������461��������
[xxxiv]��Ҋ����������Փ����̎��֮������d���������������c�F(xi��n)�����·��ҡ���������_����W(xu��)���W(xu��)������ί�T����1982���������14�����
[xxxv] ��Ҋǰ�������������43퓡�
[xxxvi] ��Ҋǰ�����������������261��263퓣�
[xxxvii]��Ҋǰ��������������354퓡�
[xxxviii]��Ҋ���¡���������.ë�נ��������������W(xu��)��Փ��������҂��g�����ɳ�����2000��棬��626-627퓡�
[xxxix] �����ձ��������r��������1�lҎ(gu��)���ġ������ֺ����c���^�e��֮؟(z��)�Θ�(g��u)��������҇��W(xu��)�ߌ���w�{�顰�`�����^�e���w؟(z��)ԭ�t�����J(r��n)�顰�`�������Ͱ������^�e��������J(r��n)���ձ������r��؟(z��)�Ό�(sh��)�H�ϲ��á��`�����w؟(z��)ԭ�t�����@�N�^�c(di��n)���ς����o(j��)90����a(ch��n)���ˏV����Ӱ�����������δ�õ���˼�c�zӑ������Ҋ�_��������Ԭ��꣺��Փ�҇������r��?sh��)�ԭ�t����������Ї����W(xu��)��1992���2�������Фᾣ���Փ�����r�������Ďׂ������^�c(di��n)��������Ї����W(xu��)��1994���4�������
��Դ�����������W(xu��)�о��������2011���1��
(������վ��ʹ�ÈDƬ��������oע����վԭ��(chu��ng)����W(w��ng)���D(zhu��n)�d�������������վ���d��(n��i)���Թ������о���Ŀ��������猦���d��(n��i)���Ю��h�����Ո(li��n)ϵ��վվ�L�������վ����(bi��o)��ԭ��(chu��ng)�����֘ӻ���������վ�Ɏ���������������D(zhu��n)�d�rՈ��(w��)��ע����̎�����ߣ���t�����䷨��؟(z��)�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