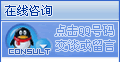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land property system of China from Public-law perspective: 1920-2010
【正文】
一、引言
從法律文本上講,今天中國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是極為明確且簡(jiǎn)單的,即分為土地的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制度,而且它們都被認(rèn)為是社會(huì)主義土地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duì)此,人們已經(jīng)耳熟能詳,然而,從制度的實(shí)際運(yùn)作來看,當(dāng)下中國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遠(yuǎn)比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要復(fù)雜。這不僅是因?yàn)閮煞N土地公有制的內(nèi)涵和性質(zhì)模糊不清,歧義叢生,以至于不但有國外研究者提出了“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的疑問(Peter Ho,2005),而且兩種土地公有制之間的邊界以及彼此關(guān)系的處理也愈加難以協(xié)調(diào),大量的社會(huì)矛盾由此滋生,并成為影響中國社會(huì)公平與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
面對(duì)這種情況,中國土地制度逐漸成為一門“顯學(xué)”,引得無數(shù)國內(nèi)外的學(xué)者紛紛加入這一研究領(lǐng)域,然而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有人試圖解決當(dāng)代中國的土地問題卻不去了解它的歷史,那么其注定是要失敗的,其研究成果要么流于俗見,無法提供真知灼見,要么夸夸其談,毫無施行之可能。
我并不想過度提及諸如“歷史昭示著未來”之類的話語,因?yàn)槿藗兛赡軙?huì)認(rèn)為過于老套。但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過往的歷史并非僅僅是塵封在書本中的談資,或者埋葬在墳?zāi)怪腥稳顺芭膶?duì)象。一些輕浮且自以為是的人認(rèn)為自己可以輕視乃至忽視歷史,徑直研究當(dāng)下土地問題并提出若干制度革新策略,但是歷史必將從書本或者墳?zāi)怪信莱鰜恚駸o所不在的幽靈一樣,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
這并不是無病呻吟,無的放矢,或者故弄玄虛,本文的研究即將表明,過去90年間中國土地產(chǎn)權(quán)所發(fā)生的每一次制度變遷,都與當(dāng)代中國土地問題密切相關(guān),它們不僅從根本上限定了當(dāng)下,而且還規(guī)定了未來可能的發(fā)展方向和路徑選擇。
為了更為清楚地說明這些問題,本文將歷史的鏡頭拉向20世紀(jì)的初期,即現(xiàn)行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產(chǎn)生、發(fā)展和變遷的起點(diǎn),試圖從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表一篇關(guān)于土地的綱領(lǐng)性文件——1920年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ì)所通過的《中國共產(chǎn)黨綱領(lǐng)》開始,透過錯(cuò)綜復(fù)雜的歷史糾葛梳理其中的脈絡(luò),并重點(diǎn)探討一下幾個(gè)問題:(1)過去90年間(1920-2010)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到底發(fā)生了哪些變化?(2)這些變化是如何發(fā)生的?(3)每一次的制度變遷給中國農(nóng)村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帶來什么樣的影響;(4)我們應(yīng)當(dāng)如何從法律上界定這些制度變遷——毫無疑問,這將成為本文的重中之重。
當(dāng)然,對(duì)這一段極為復(fù)雜的歷史進(jìn)行全面的研究既非本文可以完成的任務(wù),也并不符合我的研究主題,為此我將主要關(guān)注對(duì)土地產(chǎn)權(quán)有重大影響的制度變遷,而不是去梳理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另外,為了更加清楚地界定本文的討論范圍:有以下三個(gè)問題需要予以解釋:
首先,鑒于Demsetz將產(chǎn)權(quán)界定為一種“權(quán)利束”已經(jīng)在世界范圍內(nèi)獲得了認(rèn)同(Demsetz,1967),因此,本文在談及“土地產(chǎn)權(quán)”時(shí),傾向于強(qiáng)調(diào)其是包括所有權(quán)、使用權(quán)等權(quán)利在內(nèi)的“權(quán)利束”,而在談及“所有權(quán)”時(shí),傾向于使用嚴(yán)格法律意義上的定義,即將其定位為“一種所有權(quán)人對(duì)自己的不動(dòng)產(chǎn)或者動(dòng)產(chǎn)享有直接的全面的排他性的支配權(quán)”,具有絕對(duì)性、排他性和永續(xù)性特征的權(quán)利。不過,如同Peter Ho在他那本著名的關(guān)于中國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書中所指出地那樣,研究中國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時(shí),“所有權(quán)”與“產(chǎn)權(quán)”總是不得不交替出現(xiàn)(Peter Ho,2005),所以偶爾我也會(huì)將他們視為同義詞;
其次,我所強(qiáng)調(diào)的“公法視角”是指,我不但將利用法律的“代碼”——“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作為分析工具來完成本篇論文,而且將在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精神的指引下,側(cè)重于從對(duì)政府權(quán)力的限制和公民權(quán)利的保障角度分析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史。當(dāng)然,自從古代羅馬法中出現(xiàn)“公法與私法”的區(qū)分之后,這兩者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不但愈來愈多,而且一直飽受爭(zhēng)議,為了更加全面地討論中國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問題,我在本文中傾向于采納“調(diào)整對(duì)象說”,即凡是調(diào)整國家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律規(guī)范,都被本文視為公法規(guī)范。
最后,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香港、澳門和臺(tái)灣地區(qū)形成了與中國大陸并不相同的土地制度,因此本文所指的“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實(shí)際上僅僅包括中國大陸地區(qū)的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如果涉及到中國港澳臺(tái)地區(qū)土地問題時(shí),本文將專門注明。
二、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左右徘徊:土地公有還是私有?
盡管我并不完全贊同陳端洪先生關(guān)于“‘中國人民在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下’是當(dāng)代中國第一根本法”的判斷(陳端洪,2008),
[1]但將其用于評(píng)價(jià)20世紀(jì)以后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變遷似乎十分貼切。因?yàn)椋还苋藗兪欠癯姓J(rèn),又或者喜歡與否,中國人民確實(shí)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下對(duì)中國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作了二千年來最大的變革。這既是其無愧于“土地革命”稱號(hào)的原因,也成為今天所有土地問題的根源。只是,整個(gè)過程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簡(jiǎn)單和順利,其中依然歷經(jīng)頗多曲折。
(一)作為一種理想的土地公有制
今天的人們大概對(duì)下面的論斷不會(huì)持有太大的異議,即,作為一種試圖揭示社會(huì)發(fā)展規(guī)律,并對(duì)社會(huì)進(jìn)行全新改造的理論,“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是以消滅私有制為己任的,因?yàn)轳R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這樣寫道,
共產(chǎn)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最先進(jìn)的國家?guī)缀醵伎梢圆扇∠旅娴拇胧?.剝奪地產(chǎn),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2.征收高額累進(jìn)稅;3.廢除繼承權(quán);4.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cái)產(chǎn);5.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dú)享壟斷權(quán)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6.把全部運(yùn)輸業(yè)集中在國家手里;7.按照總的計(jì)劃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chǎn)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Marx/Engels,1872)
這一宣言為此后世界各國的共產(chǎn)黨以及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起到了“指明燈”般的指導(dǎo)作用,中國共產(chǎn)黨同樣并不例外。在1920年發(fā)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關(guān)于共產(chǎn)主義者的理想中第一條即是
對(duì)于經(jīng)濟(jì)方面的見解,共產(chǎn)主義者主張將生產(chǎn)工具—機(jī)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jī)關(guān)等—收歸社會(huì)共有,社會(huì)共用。要是生產(chǎn)工具收歸共有共用了,私有財(cái)產(chǎn)和憑銀制度就自然跟著消滅。社會(huì)上個(gè)人剝奪個(gè)人的現(xiàn)狀也會(huì)絕對(duì)沒有,因?yàn)樵斐蓜儕Z的根源的東西—剩余價(jià)值—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2]
這意味著,以“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為指導(dǎo)的中國共產(chǎn)黨早在其成立之時(shí),就十分明確地表達(dá)過其對(duì)土地問題的基本理想和基本主張,即,要在中國實(shí)行土地公有制或者“土地共有、公用”。而且直到今天,雖然土地政策和土地法律幾經(jīng)修改和完善,但其中所包含的理想從來是沒有改變的。
不過,理想歸理想,也正是因?yàn)槔硐耄钥偸悄:磺宓摹K接兄葡麥缫院笤趺崔k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宣稱,
資本因此不再是個(gè)人的,而是社會(huì)的。把資本變?yōu)楣驳摹儆谏鐣?huì)全體成員的財(cái)產(chǎn),這并不是把個(gè)人財(cái)產(chǎn)變?yōu)樯鐣?huì)財(cái)產(chǎn)。這時(shí)所改變的只是財(cái)產(chǎn)的社會(huì)性質(zhì)。它將失掉它的階級(jí)性質(zhì)。 (Marx/Engels,1872)
這段話是指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資本變?yōu)楣驳摹儆谏鐣?huì)全體成員的財(cái)產(chǎn)”呢?在法律上又應(yīng)當(dāng)如何界定呢?社會(huì)全體成員對(duì)包括土地在內(nèi)的資本是“共同共有”還是“按份共有”呢,或者就是一種抽象的盧梭式的通過“公意”載體來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共有呢?不但中國共產(chǎn)黨不很清楚,就連卡爾·馬克思,這位在伯林大學(xué)法學(xué)院就讀,最后卻拿到耶拿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學(xué)位的高材生似乎也沒有想清楚,當(dāng)然了,也許這個(gè)法律成績(jī)并不好的學(xué)生根本就沒有考慮過這個(gè)問題——青年的時(shí)候,他關(guān)心的是歷史和哲學(xué)以及詩歌問題,后來他又轉(zhuǎn)向了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研究(弗.梅林,1919)。雖然在1851年前后制定的宏偉經(jīng)濟(jì)學(xué)巨著《政治經(jīng)濟(jì)批判》的“六冊(cè)”計(jì)劃中,他打算撰寫一冊(cè)《地產(chǎn)》或者叫做《土地所有制》的專著,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計(jì)劃并沒有實(shí)現(xiàn)。
[3]所以,后來的人們總是抱怨說,雖然馬克思對(duì)資本主義私有制發(fā)起過最為猛烈的攻擊,卻不曾系統(tǒng)地、全面地闡述過未來的社會(huì)的公有制究竟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樣子。其結(jié)果是,一方面“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意”就成了爭(zhēng)論不休的問題,另一方面,這種理論的模糊性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或者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hào)的人們——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或者還有金日成,提供了廣闊的解釋和實(shí)踐空間。
(二)萬般無奈的權(quán)宜之計(jì):“土地公有”到“土地私有”
誕生于1920年代的中國共產(chǎn)黨雖然并沒有完全理解經(jīng)典馬克思作家的理論,也沒有弄清楚卡爾·馬克思所說的土地“公有”(或者“共有”)究竟是怎么樣的事情,但還是欣然接受了來自德國和俄羅斯的導(dǎo)師們的教導(dǎo),決心要沒收包括土地在內(nèi)的所有生產(chǎn)資料,以期在中國建立社會(huì)主義乃至共產(chǎn)主義。
不過,現(xiàn)實(shí)是殘酷的。它很快就發(fā)現(xiàn),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或者叫做意識(shí)形態(tài))并不被它希望拯救于水火之中的大多數(shù)中國民眾所完全接受——底層的民眾(特別是貧農(nóng)、雇農(nóng))對(duì)沒收地主的土地是極為感興趣的,但是對(duì)沒收來的土地歸蘇維埃公有而自己只享有土地使用權(quán)卻反應(yīng)十分冷淡,甚至頗為懷疑和不滿。在經(jīng)歷了土地“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nóng)民感覺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沒有權(quán)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種”之后(毛澤東,1931),共產(chǎn)黨所期望的革命斗爭(zhēng)屢戰(zhàn)屢敗。
[4]以至于當(dāng)時(shí)黨的最高領(lǐng)袖陳獨(dú)秀不得不感嘆,
農(nóng)民的私有觀念極其堅(jiān)強(qiáng),在中國,約占農(nóng)民半數(shù)之自耕農(nóng),都是中小資產(chǎn)階級(jí),不用說共產(chǎn)的社會(huì)革命是和他們的利益根本沖突,即無地之佃農(nóng),也只是半無產(chǎn)階級(jí),他們反對(duì)地主,不能超過轉(zhuǎn)移地主之私有權(quán)為他們自己的私有權(quán)的心理以上。(陳獨(dú)秀,1923)
面對(duì)理想不能實(shí)現(xiàn)和現(xiàn)實(shí)不甘妥協(xié)的困境,人們通常只有三種選擇,(1)放棄理想,遷就現(xiàn)實(shí);(2)不顧現(xiàn)實(shí),堅(jiān)持理想;(3)在不放棄理想的前提下,暫時(shí)委曲求全以等待時(shí)機(jī)的到來。逐漸成熟的中國共產(chǎn)黨選擇了第三條道路,1931年2月8日 ,蘇區(qū)中央局在第九號(hào)通告《土地問題與反富農(nóng)策略》中指出,
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的實(shí)現(xiàn) ,只有在全國蘇維埃勝利與全國工農(nóng)專政的實(shí)現(xiàn)的條件下才有可能。農(nóng)民是小私有生產(chǎn)者 ,保守私有是他們的天性 ,在他們未認(rèn)識(shí)到只有土地社會(huì)主義化 ,才是他們的經(jīng)濟(jì)出路以前 ,他們是無時(shí)不在盼望著不可求得的資本主義前途。所以 ,他們熱烈地起來參加土地革命 ,他們的目的 ,不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權(quán) ,主要的還是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權(quán)。……所以目前正是爭(zhēng)取全國蘇維埃勝利斗爭(zhēng)中,土地國有只是宣傳口號(hào),尚未到實(shí)行階段。必須使廣大農(nóng)民在革命中取得他們惟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quán),才能加強(qiáng)他們對(duì)于土地革命和爭(zhēng)取全國蘇維埃政權(quán)勝利的熱烈情緒,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中國共產(chǎn)黨蘇區(qū)中央局,1931)
后來的黨史專家們將這一封通告與毛澤東在1931年2月17日寫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題為《民權(quán)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一起列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土地政策開始由“土地公有”向“土地農(nóng)有” 轉(zhuǎn)變的標(biāo)志。此后中共內(nèi)部關(guān)于農(nóng)村土地問題的爭(zhēng)論和斗爭(zhēng)都只不過是圍繞將“誰的土地沒收再分配給什么樣的農(nóng)民”而已,農(nóng)村土地公有制不但沒有成為中共的主流話語,甚至不再被人提起,這種情況直到持續(xù)到1950年代中后期農(nóng)業(yè)高級(jí)合作社的興起。不過,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結(jié)論說,中國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放棄了“土地公有制”的理想,那很顯然是過于幼稚了。因?yàn)閷?duì)于堅(jiān)持“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中國共產(chǎn)黨來說,“土地農(nóng)有”只能是一種暫時(shí)迫不得已的妥協(xié)措施,只有“土地公有制”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這一觀點(diǎn)不但在上述提到的1931年《土地問題與反富農(nóng)策略》已經(jīng)表達(dá)清楚,而且在1934年1月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6條中得到再次重申,
中華蘇維埃政權(quán)以消滅封建剝削及徹底的改善農(nóng)民生活為目的,頒布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jí)的土地,分配給雇農(nóng)、貧農(nóng)、中農(nóng),并以實(shí)現(xiàn)土地國有為目的。
遺憾的是,中國的多數(shù)農(nóng)民,甚至黨和軍隊(du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完全明白這個(gè)道理。他們對(duì)共產(chǎn)黨土地政策和法律的了解,主要來自共產(chǎn)黨的“打土豪,分田地”口號(hào)宣傳和實(shí)際行動(dòng)。為了保護(hù)“革命的果實(shí)”,也就是保護(hù)已經(jīng)和即將取得所有權(quán)的土地,他們“翻身鬧革命”,積極參軍參戰(zhàn),發(fā)展生產(chǎn),經(jīng)過八年抗日和三年國內(nèi)戰(zhàn)爭(zhēng),最終用“幾千萬革命先烈換來了紅色江山”。
1949年9月,中國共產(chǎn)黨取得了國家的政權(quán),但它認(rèn)為這僅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不是“全國工農(nóng)專政的實(shí)現(xiàn)”——不但中央政府是由代表社會(huì)各個(gè)基層的多黨聯(lián)合組成,而且這個(gè)新生政權(quán)也并不鞏固,因此它沒有提起過有關(guān)“土地公有化”的議題。在土地政策上,除了沒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大陸的土地,規(guī)定“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鹽田和礦山及湖、沼、河、港等,均歸國家所有”,并要求“分配土地時(shí),縣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據(jù)當(dāng)?shù)赝恋厍闆r,酌量劃出一部分土地收歸國有,作為一縣或數(shù)縣范圍內(nèi)的農(nóng)事試驗(yàn)場(chǎng)或國營求救農(nóng)場(chǎng)之用”以外,
[5]中國共產(chǎn)黨主要是忙著為實(shí)現(xiàn)土地的農(nóng)民所有,即為實(shí)現(xiàn)“耕者有其田”而奮斗。為此,1949年10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通過的《共同綱領(lǐng)》第3條宣布,
要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yōu)檗r(nóng)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hù)國家的公共財(cái)產(chǎn)和合作社的財(cái)產(chǎn),保護(hù)工人、農(nóng)民、小資產(chǎn)階級(jí)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jí)的經(jīng)濟(jì)利益及其私有財(cái)產(chǎn)。
到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實(shí)施,雖然該部法律被稱為“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中國人民對(duì)于殘余的封建制度所發(fā)動(dòng)的一場(chǎng)最猛烈的經(jīng)濟(jì)的政治的戰(zhàn)爭(zhēng)”,“將在實(shí)際上結(jié)束中國社會(huì)的半封建性質(zhì)”(轉(zhuǎn)引自新華書店山東總分店編輯部,1950),但按照毛澤東“消滅封建制度,保存富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要求,該法(第2、4、6條)不但要“保護(hù)富農(nóng)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cái)產(chǎn),不得侵犯”,而且只可以“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nóng)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nóng)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cái)產(chǎn)不予沒收。”另外,對(duì)于“地主兼營的工商業(yè)及其直接用于經(jīng)營工商業(yè)的土地和財(cái)產(chǎn),不得沒收。不得因沒收封建的土地財(cái)產(chǎn)而侵犯工商業(yè)。工商業(yè)家在農(nóng)村中的土地和原由農(nóng)民居住的房屋,應(yīng)予征收。但其在農(nóng)村中的其他財(cái)產(chǎn)和合法經(jīng)營,應(yīng)加保護(hù),不得侵犯。”這不但意味著農(nóng)村地區(qū)“農(nóng)民土地所有制”得到法律的承認(rèn)和保護(hù),也意味著在城市,包括工商業(yè)者在內(nèi)的城市居民的私有房屋和土地所有權(quán)也將得到尊重和保護(hù)。
1954年9月,新中國頒布了第一部正式憲法,該憲法在第8條和第13條不但規(guī)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hù)農(nóng)民的土地所有權(quán)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所有權(quán)”,而且規(guī)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對(duì)城鄉(xiāng)土地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實(shí)行征購、征用或者收歸國有。”這使得城鄉(xiāng)土地私有制得到根本法的再次確認(rèn)。
[6]當(dāng)然確認(rèn)的方式并不相同,前者是明確規(guī)定,后者則只是默認(rèn),這為后來中國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發(fā)展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三)理想與信念的再次高昂:“土地私有”向“土地公有”的回歸
土地歸農(nóng)民個(gè)體所有,極大地刺激了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的發(fā)展,1952年的全國糧食產(chǎn)量是16392萬噸,比1949年增長44.8%,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9.3%。棉花產(chǎn)量則達(dá)到130.4萬噸,比1949年增加193.7%,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53%(國家統(tǒng)計(jì)局,1983) 。但是,“土地歸農(nóng)”同樣出現(xiàn)了引發(fā)了一些問題,使得中共認(rèn)為有必要對(duì)之進(jìn)行社會(huì)主義改造。依據(jù)當(dāng)時(shí)中共中央的認(rèn)識(shí),主要有以下兩個(gè)方面的原因:
(1)“農(nóng)民個(gè)體所有土地,家庭自主經(jīng)營”的模式與社會(huì)主義即將開始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不相適應(yīng)。在中共領(lǐng)導(dǎo)人,特別是毛澤東看來,小農(nóng)個(gè)體經(jīng)濟(jì)不但難以滿足城市和工業(yè)對(duì)糧食和農(nóng)產(chǎn)品不斷增長的需求,也使國家的工業(yè)品難以獲得市場(chǎng),更為重要的是,其難以提供工業(yè)發(fā)展所需要的大量資金積累。雖然在1927年《湖南農(nóng)民運(yùn)動(dòng)考察報(bào)告》撰寫時(shí),毛澤東就已經(jīng)把中國農(nóng)民當(dāng)成中國革命運(yùn)動(dòng)的核心,并因?yàn)檫@一正確認(rèn)識(shí)贏得了黨內(nèi)的領(lǐng)導(dǎo)地位,最終帶領(lǐng)中國農(nóng)民打下江山,但他并不認(rèn)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功臣階級(jí)”會(huì)自然而然成為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中的“先進(jìn)階級(jí)”——要知道,“革命”與“建設(shè)”的邏輯并不一樣。
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看來,當(dāng)時(shí)中國的農(nóng)民以及其從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是“落后的”,“和古代沒有多大區(qū)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僅僅在于其廢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逐步向著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可能性”。但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xiàn)實(shí),“必須謹(jǐn)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dǎo)它們向著現(xiàn)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fā)展”。為此,毛告誡全黨,與將來的現(xiàn)代化相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設(shè))道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只有快速實(shí)現(xiàn)國家的工業(yè)化,特別是重工業(yè)化,社會(huì)主義才能早日建成(毛澤東,1949)。近代以來,中國人所追求的國富民強(qiáng)才能實(shí)現(xiàn),為此而犧牲農(nóng)民的土地私有權(quán)是必要的,況且這也是帶領(lǐng)他們奔向更加美好的社會(huì)所必須的。
(2)土地改革以后出現(xiàn)了新的貧富分化和土地集中則是需要實(shí)行土地公有制的另一主要原因,據(jù)山西省忻縣地委在1953年前后對(duì)143個(gè)農(nóng)村的調(diào)查顯示,
土改后,已有8253戶農(nóng)民出賣土地39912畝,出賣土地占賣地戶每戶平均土地的28%,占總土地的5.5%。另外,從出賣土地的時(shí)間來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shì)。在49個(gè)村農(nóng)民出賣的10784畝土地中,1949年出賣的占3.95%,1950年出賣的占30.99%,1951年出賣的占51.15%。據(jù)靜樂縣五區(qū)(老區(qū))19個(gè)村的統(tǒng)計(jì),在880戶賣房地的農(nóng)民中,有167戶老中農(nóng)因出賣土地下降為貧農(nóng),471戶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的新中農(nóng)因出賣土地又恢復(fù)到貧農(nóng)的地位,調(diào)查組得出結(jié)論,認(rèn)為“三年來農(nóng)村階級(jí)分化的速度是迅速的,從地區(qū)上說是普通的,分化的面也很大。” (轉(zhuǎn)引自史敬堂等,1959)
[7]
如果從常理出發(fā),這種因?yàn)榧膊 ⑺劳觥?zāi)難以及勞動(dòng)技能高低而引發(fā)的貧富分化和土地集中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沒有值得大驚小怪的。然而如果放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的框架下,我們發(fā)現(xiàn)問題似乎變得嚴(yán)重起來,因?yàn)樨毟环只坏c革命的理想(平均地權(quán))不相符合,而且直接否定了革命的必要性——在中國共產(chǎn)黨看來,至少在毛澤東看來,其所領(lǐng)導(dǎo)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zhēng)之所以不只是一次農(nóng)民起義,而是一次偉大的“革命”,其偉大意義不僅僅在于實(shí)現(xiàn)了政權(quán)的更替和國家的獨(dú)立,而且是“一個(gè)全新的開始”,是“一個(gè)獨(dú)一無二的、不可重復(fù)的事件”,要實(shí)現(xiàn)整個(g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革命,要消滅任何可能的剝削,讓民眾擺脫貧困,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
[8]由于建國初土地改革所確立的“土地農(nóng)民所有制”不過是為農(nóng)民競(jìng)爭(zhēng)重新劃了一條新的起跑線,卻并沒有消除以土地私有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和農(nóng)民競(jìng)爭(zhēng)模式,因此任其自由發(fā)展下去,必然又將會(huì)回到貧富分化、土地兼并的老路上,那革命的意義在哪里呢?那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農(nóng)民革命與歷史上的農(nóng)民起義又有什么區(qū)別呢?毛提出,
現(xiàn)在農(nóng)民賣地,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nóng)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nóng)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才可使得農(nóng)民不必出租土地了。(毛澤東,1953)
由于接下來的歷史涉及到了農(nóng)村和城市的二元土地產(chǎn)權(quán)體制,因此我將在梳理歷史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分別進(jìn)行分析。
三、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史的梳理
在1951年前后,關(guān)于是否直接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直接進(jìn)行農(nóng)業(yè)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即將作為“生產(chǎn)資料的土地”(農(nóng)地)收歸勞動(dòng)群眾集體所有,在國內(nèi)和黨內(nèi)引起了巨大的爭(zhēng)論。爭(zhēng)論的結(jié)果今天的人們已經(jīng)熟知,但是農(nóng)地集體化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伴隨著多元力量的博弈和斗爭(zhēng),這一過程大致經(jīng)過了初級(jí)社、高級(jí)社、人民公社和1982年憲法修改四個(gè)階段中若干步驟才逐步完成的(參見圖表1)。
[9]
圖表 1 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史(1949-2010)。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中國地域過于遼闊,而且各個(gè)地方的情況差別很大,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制度變遷時(shí)間因此并不完全一致,這導(dǎo)致提供制度變遷的準(zhǔn)確時(shí)間幾乎不太可能,所以只能提供大概的年份和時(shí)間段。
(一)初級(jí)社:“土地所有權(quán)歸農(nóng)”
隨著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逐步恢復(fù)到了戰(zhàn)前水平,以山西省為代表的一些革命老區(qū)領(lǐng)導(dǎo)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中間出現(xiàn)了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jìn)取地現(xiàn)象,勞動(dòng)互助組不但不能激發(fā)農(nóng)民進(jìn)一步發(fā)展生產(chǎn)的激情,反而出現(xiàn)了“有些常年互助組改為臨時(shí)互助組,有些臨時(shí)互助組自行解散”的情況,甚至山西襄垣縣一個(gè)農(nóng)村黨支部書記公開宣布,
我們支部參加了抗日、打老蔣,現(xiàn)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蔣都打倒了,任務(wù)完成了,所以我們的支部宣布解散。(轉(zhuǎn)引自王里鵬,2009)
針對(duì)這種現(xiàn)象,東北、山西等地區(qū)的主要領(lǐng)導(dǎo)干部認(rèn)為,農(nóng)民和農(nóng)業(yè)不是朝著社會(huì)主義所要求的現(xiàn)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fā)展,而是向著富農(nóng)的方向發(fā)展,并將這種現(xiàn)象看作是互助組發(fā)生渙散現(xiàn)象的最根本原因。他們開始考慮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和組織形式,在經(jīng)濟(jì)上把農(nóng)民組織起來,使黨在政治上繼續(xù)領(lǐng)導(dǎo)農(nóng)民沿著一條正確的道路前進(jìn)的問題。(轉(zhuǎn)載自姚力文、劉建平,2009;苗長青,2004)在否定了農(nóng)會(huì)和蘇聯(lián)式集體農(nóng)莊以后,山西省的領(lǐng)導(dǎo)人從1946年平順縣青春凹農(nóng)民自發(fā)創(chuàng)辦的土地合作社得到啟示,建議“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把互助運(yùn)動(dòng)提高一步”,他們認(rèn)為,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雖然和互助組同是建筑在個(gè)體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之上的集體勞動(dòng)組織,但是由于它實(shí)行了土地入股、統(tǒng)一經(jīng)營、收獲物為統(tǒng)一按勞力與土地分配的原則,因而它就比互助組更能發(fā)揮土地的生產(chǎn)效能與勞動(dòng)的積極性,就有可能按照各人的特長比互助組更加廣泛地改進(jìn)與提高耕作技術(shù)。(轉(zhuǎn)引自史敬堂,1959)
不過,山西試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的工作一開始并沒有引起掌聲和支持,而是遭到了華北局和時(shí)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批評(píng),華北局和劉少奇(1951)認(rèn)為,農(nóng)業(yè)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yè)化和使用機(jī)器耕種以及土地國有為條件。在這些條件沒有成熟之前就動(dòng)搖、削弱乃至否定土地私有制是“錯(cuò)誤的、危險(xiǎn)的、空想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主義思想”(轉(zhuǎn)載自姚力文、劉建平,2009),不過毛澤東卻對(duì)山西表示了支持的意見,他論證到,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有一個(gè)工場(chǎng)手工業(yè)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dòng)力機(jī)械、而依靠工場(chǎng)分工以形成新生產(chǎn)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tǒng)一經(jīng)營形成新生產(chǎn)力,去動(dòng)搖私有基礎(chǔ),也是可行的。
[10]
于是,山西省關(guān)于初級(jí)社的實(shí)驗(yàn)和經(jīng)驗(yàn)因?yàn)楂@得最高領(lǐng)袖的支持而得以推行。1951年9月,毛澤東繞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的全體會(huì)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huì)(分別為當(dāng)時(shí)國家的立法機(jī)關(guān)和行政機(jī)關(guān))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為黨的最高政策制定機(jī)關(guān)和執(zhí)行機(jī)關(guān)),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召集地方部門代表參加的互助合作會(huì)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該草案把簡(jiǎn)單勞動(dòng)互助、常年互助組、實(shí)行土地入股與公共積累的生產(chǎn)合作社總結(jié)為在集體化方向前進(jìn)的道路上”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級(jí)到高級(jí)”三種形式,要求各地不能片面提倡“發(fā)家致富的口號(hào)”,而要“在農(nóng)村中提出愛國的口號(hào),使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和國家的要求聯(lián)系起來”,并將生產(chǎn)合作化“當(dāng)作一件大事”去組織和實(shí)行。
[11]盡管這一草案直到1953年2月才通過中共中央正式討論通過,但在1951年底的時(shí)候,已經(jīng)在全國迅速推行開來。
在“初級(jí)社”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政策中,有以下三點(diǎn)特征是需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1)農(nóng)民是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初級(jí)社的,土地所有權(quán)仍歸個(gè)人私有,并可以根據(jù)自愿的原則退股;(中共中央,1951)(2)可以入股的生產(chǎn)資料除了土地、農(nóng)業(yè)設(shè)備以外,還包括勞動(dòng)力,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后者甚至是最為重要的生產(chǎn)資料。因此中共中央在1953年時(shí)提出,“必須隨著生產(chǎn)的增長、勞動(dòng)效率的發(fā)揮和群眾的覺悟,逐步而穩(wěn)妥地提高勞動(dòng)報(bào)酬的比例。”(中共中央,1953)全國各地也紛紛制定了“勞力分紅”高于“土地分紅”的政策。
[12]這一理論的實(shí)施,不但忽視了土地自身具有的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而且為后來的高級(jí)社“取消土地分紅”埋下伏筆;(3)由于執(zhí)政集團(tuán)認(rèn)為農(nóng)民既看不清歷史的趨勢(shì),也看不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需要引導(dǎo)甚至強(qiáng)迫他們參加初級(jí)社,山西省委領(lǐng)導(dǎo)引用恩格斯理論來證明初級(jí)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證明了這一點(diǎn)。
[13]
(二)高級(jí)社:按份共有的集體土地所有制
1951年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不但肯定了山西等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的試驗(yàn),而且還明確指出,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雖然是互助運(yùn)動(dòng)在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高級(jí)形式,但是比起完全的社會(huì)主義的集體農(nóng)莊(即是更高級(jí)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這還是較低級(jí)的形式,因此,它還只是走向社會(huì)主義農(nóng)業(yè)的過渡的形式。
這意味著,中國新民主主義向社會(huì)主義的過渡,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事實(shí)上從1951年就開始了。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huì)議提出了著名的“過渡時(shí)期總路線”設(shè)想,依據(jù)該路線的設(shè)想,中國需要在“要在一個(g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期內(nèi),逐步實(shí)現(xiàn)國家的社會(huì)主義工業(yè)化,并逐步實(shí)現(xiàn)國家對(duì)農(nóng)業(yè)、對(duì)手工業(yè)和對(duì)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這個(g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期”被當(dāng)時(shí)的領(lǐng)導(dǎo)人設(shè)想為“需要10到15年的時(shí)間或更多一些時(shí)間”,
[14]同年12月,中共中央將“農(nóng)民這種在生產(chǎn)上逐步聯(lián)合起來的具體道路”明確總結(jié)為,
就是經(jīng)過簡(jiǎn)單的共同勞動(dòng)的臨時(shí)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dòng)的基礎(chǔ)上實(shí)行某些分工分業(yè)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cái)產(chǎn)的常年互助組,到實(shí)行土地入股、統(tǒng)一經(jīng)營而有較多公共財(cái)產(chǎn)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到實(shí)行完全的社會(huì)主義的集體農(nóng)民公有制的更高級(jí)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也就是集體農(nóng)莊)。這種由具有社會(huì)主義萌芽、到具有更多社會(huì)主義因素、到完全的社會(huì)主義的合作化的發(fā)展道路,就是我們黨所指出的對(duì)農(nóng)業(yè)逐步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改造的道路。(中共中央,1953)
到1956年6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三次會(huì)議正式通過了《高級(jí)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示范章程》,使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合作成為一項(xiàng)正式的法律制度。就土地產(chǎn)權(quán)問題而言,該章程做了如下規(guī)定:
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按照社會(huì)主義的原則,把社員私有的主要生產(chǎn)資料,即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農(nóng)具,取消土地報(bào)酬,轉(zhuǎn)為合作社集體所有,實(shí)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②社員私有的生活資料和零星的樹木、家禽、家畜、小農(nóng)具、經(jīng)營家庭副業(yè)所需要的工具,仍屬社員私有,都不入社;③從事城市的職業(yè)、全家居住在城市的人,或者家居鄉(xiāng)村、勞動(dòng)力外出、家中無人參加勞動(dòng)的人,屬于他私有的在農(nóng)村中的土地,可以交給合作社使用。如果本主移居鄉(xiāng)村,或者外出的勞動(dòng)力回到鄉(xiāng)村,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應(yīng)該吸收他入社。如果他不愿意入社,合作社應(yīng)該把原有的土地或者同等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土地給他;④要求退社的社員一般地要到生產(chǎn)年度完結(jié)以后才能退社。社員退社的時(shí)候,可以帶走他入社的土地或者同等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土地,可以抽回他所交納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資。
[15]
從這一規(guī)定中,我們可以看出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具有了如下特征:(1)土地由農(nóng)民個(gè)體所有變?yōu)檗r(nóng)民勞動(dòng)群眾集體所有,而且該集體所有制的性質(zhì)是明確的——即以“按份共有”為基礎(chǔ)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單個(gè)農(nóng)民將其受法律保護(hù)的土地所有權(quán)入股加入集體,
[16]并且依據(jù)其所具有的股權(quán)與其他農(nóng)民一起共同對(duì)集體土地享有所有權(quán),其可在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條件下依照其所享有的份額請(qǐng)求分割“入社的土地或者同等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土地”的所有權(quán);(2)農(nóng)民只是以作為生產(chǎn)資料的土地入股參加生產(chǎn)合作社的,對(duì)于住房、宅基地等作為生活資料的房產(chǎn)和地產(chǎn)依然是農(nóng)民私有的;(3)雖然高級(jí)社已經(jīng)是完全社會(huì)主義性質(zhì)了,但實(shí)行的只是勞動(dòng)群眾集體所有制,而非土地國有制。
[17]
1956年1月以后,將互助組、初級(jí)社改造升級(jí)為高級(jí)社運(yùn)動(dòng)在全國掀起熱潮,到該年年底,全國參加高級(jí)社的農(nóng)戶就已占全國農(nóng)戶總數(shù)的87.8%。
[18]不過,高級(jí)社并沒有為多數(shù)農(nóng)民所真正理解和支持,1956年秋冬之后,全國各地紛紛出現(xiàn)退社事件。
[19]
(三)人民公社:抽象的集體所有及其帶來的問題
盡管高級(jí)社遭到了黨內(nèi)干部和農(nóng)民的抵制,領(lǐng)袖也曾一度認(rèn)為“任何過‘左’的政策,都會(huì)破壞與中農(nóng)的合作”,但是對(duì)于共產(chǎn)主義的理想和狂熱最終還是戰(zhàn)勝了理性的思考,在將所有的反對(duì)意見都打到和消滅之后,
[20]毛稍作休息,又發(fā)動(dòng)了人民公社運(yùn)動(dòng)。這一運(yùn)動(dòng)并沒有認(rèn)真總結(jié)農(nóng)業(yè)合作化以來的教訓(xùn),反而通過意識(shí)形態(tài)的強(qiáng)化進(jìn)一步實(shí)現(xiàn)了土地的公有制。
1958年8月,依據(jù)毛澤東在河南新鄉(xiāng)縣七里營關(guān)于“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中共中央通過了《關(guān)于在農(nóng)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認(rèn)為,
人民公社是形勢(shì)發(fā)展的必然趨勢(shì)。……有不可阻擋之勢(shì)。人民公社發(fā)展的主要基礎(chǔ)是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全面的不斷的躍進(jìn)和五億農(nóng)民愈來愈高的政治覺悟……建立農(nóng)林牧副漁全面發(fā)展、工農(nóng)商學(xué)兵互相結(jié)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dǎo)農(nóng)民加速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提前建成社會(huì)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但)實(shí)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jīng)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fā)展中繼續(xù)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
[21]
中共中央的決議下發(fā)以后,很快傳到全國各地的田間地頭,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化運(yùn)動(dòng)開始了。1958年8月到10月,全國74萬個(g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合并成26000多個(gè)人民公社,全國農(nóng)村基本上實(shí)現(xiàn)了人民公社化。
[22]與“高級(jí)社”相比,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發(fā)生了三個(gè)方面巨大的變化:
(1)在高級(jí)社體制下,農(nóng)民只要將作為生產(chǎn)資料的農(nóng)用地交給農(nóng)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即可,私有房屋以及其地基依然是私有的,然而,人民公社體制卻要求社員,
根據(jù)共產(chǎn)主義大協(xié)作的精神,應(yīng)將包括土地在內(nèi)的一切公有財(cái)產(chǎn)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bǔ)。在己經(jīng)基本上實(shí)現(xiàn)了生產(chǎn)資料公有化的基礎(chǔ)上,社員轉(zhuǎn)入公社,應(yīng)該交出自留地,并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chǎn)資料轉(zhuǎn)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畜仍歸個(gè)人所有。
[23]
按照經(jīng)典馬克思的理論,之所以出現(xiàn)剝削和社會(huì)不公,是因?yàn)樯鐣?huì)成員占有生產(chǎn)資料不均造成的,生活資料—比如“私有房基”并不屬于應(yīng)該“被集體化”的對(duì)象,然而在即將進(jìn)入共產(chǎn)主義的熱情的感召下,“私有房基”居然也被塞進(jìn)“生產(chǎn)資料”中“被公有”了,這為后來的禁止農(nóng)村宅基地買賣以及商品房建設(shè)等問題的出現(xiàn)埋下伏筆。
(2)在高級(jí)社體制下,土地產(chǎn)權(quán)是明確的,即“按份共有”的股份合作制,不但社員有退社并帶走土地的自由,而且不同高級(jí)社之間的土地也可以相互買賣(但不可以無償占有)。人民公社體制下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zhì)卻變得模糊——社員將土地交給公社,卻“多者不退,少者不補(bǔ)”,而且還喪失了退社和帶走土地的自由。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宣布“共產(chǎn)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jīng)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fā)展中繼續(xù)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這使得包括土地在內(nèi)的公社生產(chǎn)資料集體所有制一躍成為公法上的集體所有,其如同國家所有權(quán)一樣,既不接受私法的調(diào)整,也無法按照私法的理論來解釋——直到今天,我們也沒有辦法在民法關(guān)于所有權(quán)的性質(zhì)中找到其應(yīng)有的位置,關(guān)于這一問題,后文將重點(diǎn)分析,此處不再贅言。
(3)由于公社主要領(lǐng)導(dǎo)多是由上級(jí)派來“國家干部”,主要工作是召開會(huì)議以落實(shí)中央和上級(jí)指示精神,所以相比保留農(nóng)民身份,拿生產(chǎn)隊(duì)工分的大隊(duì)干部,他們對(duì)土地和農(nóng)民的感情十分疏遠(yuǎn),卻可以按照“平均主義和無償調(diào)撥物資”(簡(jiǎn)稱“一平二調(diào)”)的原則隨意調(diào)配不同高級(jí)社的土地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因此出現(xiàn)了大量隨意征調(diào)土地的行為,原本性質(zhì)模糊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因此變得更加混亂。學(xué)者張樂天在其對(duì)浙江省海寧縣人民公社的研究中細(xì)致地討論了此一問題,他談到,
人民公社隨時(shí)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占用管轄范圍內(nèi)的任何一塊土地。土地的占用沒有規(guī)定的手續(xù),甚至沒有正式備案的文件。土地征用盡管經(jīng)過了大隊(duì)干部的同意,但這實(shí)際上是做做“表面文章”。公社用地是“事業(yè)的需要”,大隊(duì)干部不僅必須同意將世代屬于他們的土地劃出,而且必須馬上同意。同意不同意是一個(gè)政治問題,誰也不會(huì)為保護(hù)已經(jīng)不屬于自己的東西而去犯政治錯(cuò)誤。……1958年12月,公社成立伊始,就從L、聯(lián)新大隊(duì)劃出數(shù)十畝土地辦起了名不副實(shí)的“錢塘江大學(xué)”。1959年10月,公社更是劃出數(shù)百畝土地創(chuàng)辦錢塘江公社蠶種場(chǎng)。(張樂天,1998)
H. Demsetz曾論證說,
在魯賓遜的世界里產(chǎn)權(quán)是沒有必要的。產(chǎn)權(quán)是一種社會(huì)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在事實(shí)上能幫助一個(gè)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jìn)行交易時(shí)的合理預(yù)期。……新的產(chǎn)權(quán)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們對(duì)新的成本-受益可能的渴望進(jìn)行調(diào)整的反應(yīng)。(Demsetz, 1967)
看來他并非完全正確,在1960年代中國人對(duì)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追求中,土地產(chǎn)權(quán)確實(shí)是一種社會(huì)工具,但既不能幫助人們形成合理的預(yù)期,也不是理性的反應(yīng)。
(4) “共產(chǎn)風(fēng)”、“亂指揮”加上“大躍進(jìn)”運(yùn)動(dòng)中的種種激進(jìn)政策,引起了農(nóng)民(包括一部分生產(chǎn)大隊(duì)干部)的嚴(yán)重不滿造成,他們不但如同斯科特(James C. Scott,1977)筆下的馬來西亞農(nóng)民一樣,“用嘲笑、粗野、諷刺、不服從的小動(dòng)作,偷懶、裝糊涂、假裝順從、裝傻賣呆、偷盜、怠工、誹謗、暗中破壞等等”行動(dòng)表示抗議,
[24]而且試圖進(jìn)行“責(zé)任田”、“分田到戶”等土地制度改革,盡管這種自發(fā)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最終被強(qiáng)制性中斷,
[25]卻也迫使中共中央在人民公社的經(jīng)濟(jì)政策上,特別是土地政策上一再退讓——從開始的“三級(jí)所有,以社為基礎(chǔ)”,變?yōu)椤叭?jí)所有,以生產(chǎn)大隊(duì)為基礎(chǔ)”,后來又改為“三級(jí)所有,以生產(chǎn)隊(duì)為基礎(chǔ)”。政策的不斷調(diào)整雖然有利于生產(chǎn)的恢復(fù)和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但是同時(shí)也加劇了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混亂,而且最終使農(nóng)村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變得面目全非。
1959年2月底的“第二次鄭州會(huì)議”通過的《關(guān)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guī)定(草案)》規(guī)定,“規(guī)模相當(dāng)于原高級(jí)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的管理區(qū)和生產(chǎn)大隊(duì),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稱,以“生產(chǎn)大隊(duì)為基礎(chǔ)的三級(jí)所有制從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變(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gè)五年計(jì)劃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堅(jiān)決不變)。”
[26]不過,到了1961年10月,中央對(duì)這一規(guī)定又作了修改,將產(chǎn)權(quán)制度修改為“三級(jí)所有,以生產(chǎn)隊(duì)為基礎(chǔ)”,并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改變農(nóng)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和《農(nóng)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兩個(gè)文件中進(jìn)一步肯定這種制度,
生產(chǎn)隊(duì)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它實(shí)行獨(dú)立核算,自負(fù)盈虧,直接組織生產(chǎn),組織收益的分配。這種制度定下來以后,至少三十年不變。……生產(chǎn)隊(duì)范圍內(nèi)的土地,都?xì)w生產(chǎn)隊(duì)所有。生產(chǎn)隊(duì)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zhǔn)出租和出賣。
[27]
從此以后,除了局部地區(qū)出現(xiàn)過短暫“回潮”以外,“三級(jí)所有、三級(jí)管理”的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就基本確定下來。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集體之間的土地所有權(quán)關(guān)系就明確了。因?yàn)?962年的《修正草案》同時(shí)又規(guī)定,
有些地方的土地,由于各種原因,幾年來變動(dòng)很大,各隊(duì)之間過于懸殊,群眾要求調(diào)整的,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調(diào)整,但是不要打亂重分。土地的所有權(quán)歸誰,可以斟酌情況決定。在有利于改良土壤、培養(yǎng)地力、保持水土和增加水利建設(shè)等前提下,可以確定歸生產(chǎn)隊(duì)所有,也可以仍舊歸大隊(duì)所有,固定給生產(chǎn)隊(duì)長期使用。
使用如此含糊的語言來當(dāng)作土地所有權(quán)界定的標(biāo)準(zhǔn)當(dāng)然迫不得已的苦衷,但也使得后來的人們不但難以界定某一地塊當(dāng)初是屬于哪個(gè)農(nóng)民私有,甚至連屬于哪一個(gè)高級(jí)社擁有所有權(quán)也界定不清楚了。
(四)后人民公社時(shí)代:我們保留了什么?
當(dāng)歷史的車輪走到1976年時(shí),隨著領(lǐng)袖的去世、“四人幫”的倒臺(tái)和“文化大革命”的結(jié)束,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逐步掀開新的一頁,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也在發(fā)生著新的變遷。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huì),并通過《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和完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zé)任制的幾個(gè)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同意,
在那些邊遠(yuǎn)山區(qū)和貧困落后的地區(qū),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chǎn)靠貸款,生活靠救濟(jì)”的生產(chǎn)隊(duì),群眾對(duì)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chǎn)到戶的,應(yīng)當(dāng)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chǎn)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gè)較長的時(shí)間內(nèi)保持穩(wěn)定……(轉(zhuǎn)引自杜潤生,2005)
后來的實(shí)踐證明了,那些率先實(shí)行包產(chǎn)到戶的貧困省份比相對(duì)富裕但依然堅(jiān)守舊體制的省份發(fā)展更快,所以“包產(chǎn)到戶、包干到戶”逐步在全國建立起來,最終發(fā)展完善成為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生產(chǎn)責(zé)任制,即農(nóng)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chǎn)資料和生產(chǎn)任務(wù)的一種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zé)任制形式。這種土地經(jīng)營模式的改變不但激發(fā)了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熱情,極大促進(jìn)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而且使得人民公社體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1982年憲法規(guī)定,按照政社分開的原則,中國恢復(fù)鄉(xiāng)級(jí)政府的設(shè)置,在城市和農(nóng)村按居民居住地區(qū)設(shè)居民委員會(huì)或者村民委員會(huì),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農(nóng)村人民公社、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合作社經(jīng)濟(jì),僅僅作為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而存在。
[28] 198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wù)院規(guī)定,鄉(xiāng)的規(guī)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轄范圍為基礎(chǔ),如原有公社范圍過大的也可以適當(dāng)劃小,村民委員會(huì)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應(yīng)按村民居住狀況設(shè)立。有些以自然村為單位建立了農(nóng)業(yè)合作社等經(jīng)濟(jì)組織的地方,當(dāng)?shù)厝罕娫敢鈱?shí)行兩個(gè)機(jī)構(gòu)一套班子,兼行經(jīng)濟(jì)組織和村民委員會(huì)的職能,也可同意試行。
[29]1993年憲法修改時(shí),將“農(nóng)村人民公社、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修改為“農(nóng)村中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為主的責(zé)任制”,
[30]從此,“人民公社”在中國的法律中消失。
不過,這僅僅是一段歷史而非所有問題的終結(jié)。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對(duì)建國三十多年間的土地政策做了如下評(píng)述,
建國三十二年來,我們?nèi)〉玫闹饕删褪牵骸摹⒔⒑桶l(fā)展了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基本上完成了對(duì)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基本上實(shí)現(xiàn)了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
[31]
就這樣,公社解體了,農(nóng)民們獲得了土地的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但公社體制下的土地集體制度卻得以保留,而且形成了一種既不同于合作化之前“農(nóng)民個(gè)體所有,家庭自主經(jīng)營”模式,也不同于“勞動(dòng)群眾集體所有,勞動(dòng)群眾集體經(jīng)營”模式的“勞動(dòng)群眾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jīng)營”模式——1986年制定并在今天依然實(shí)行的《土地管理法》(第10條)將其表達(dá)為“農(nóng)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nóng)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huì)經(jīng)營、管理;已經(jīng)分別屬于村內(nèi)兩個(gè)以上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農(nóng)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nèi)各該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jīng)營、管理;已經(jīng)屬于鄉(xiāng)(鎮(zhèn))農(nóng)民集體所有的,由鄉(xiāng)(鎮(zhèn))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經(jīng)營、管理。”
作為公社體制的“遺產(chǎn)”,這種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為1980年以后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但是也為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明晰帶來了無窮的苦惱,更為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益的保護(hù)留下了許多無法破解的難題。
四、如何解釋90年來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變遷?
上述發(fā)生在20世紀(jì)中國的故事,總是讓中外飽學(xué)之士狼狽不堪,也讓人們對(duì)于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變革增加了頗多好奇。可以想象,人們總會(huì)忍俊不禁地追問:這一切都是為什么呢?為什么20世紀(jì)以來的中國發(fā)生了這樣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遷,而不選擇其他道路呢?為什么靠“打土豪、分田地”獲得農(nóng)民支持的中國共產(chǎn)黨就一定要選擇土地公有制呢?那些為了獲得土地私有權(quán)翻身鬧革命的中國農(nóng)民,為什么不像蘇聯(lián)農(nóng)民一樣為了保護(hù)自己剛剛到手的土地所有權(quán)而激烈的抵抗呢?
本文既沒有雄心全面系統(tǒng)地回答上述問題,也沒有找到完全解答這些疑問的方法。不過我相信,“意識(shí)形態(tài)-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權(quán)利-義務(wù)”兩個(gè)分析框架可能會(huì)幫助人們從側(cè)面理解過去90年間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所發(fā)生的變遷。
(一)近現(xiàn)代中國的意識(shí)形態(tài):國富民強(qiáng)與馬克思主義
如果從宏觀上看,1840年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后的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被西方資本主義列強(qiáng)侵略的屈辱史。也正是從此時(shí)起,如何恢復(fù)中華帝國的榮光,找到作為一個(gè)民族應(yīng)有的尊嚴(yán),實(shí)現(xiàn)國家富強(qiáng)和人民富裕,就籠罩在中國有責(zé)任感的政治、文化和資本精英們的心頭,儼然成為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即民族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盡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一意識(shí)形態(tài)表現(xiàn)為不同的要求——戊戌變法到抗日戰(zhàn)爭(zhēng)(1898-1945)期間,主要表現(xiàn)為“救亡圖存,保國保種”的追求主權(quán)獨(dú)立的歷次運(yùn)動(dòng)、革命與戰(zhàn)爭(zhēng);1949年以后則表現(xiàn)為如何在一個(gè)政治獨(dú)立的國家框架內(nèi)擺脫貧困,并以大國的身份與世界其他民族在世界并肩而立,但“追求富強(qiáng)”的理想是不曾改變的,以至于近代以來作為整體的中國人對(duì)于幾乎每一個(gè)問題的把握與分析,判斷與取舍,都無不帶有此一印記,而且直到今天,這種情況并沒有多大的變化。在這個(gè)意義上,“國富民強(qiáng)”儼然成為近現(xiàn)代中國的終極意識(shí)形態(tài)。
持中而論,這一意識(shí)形態(tài)為1840年以后中國的轉(zhuǎn)型做出決定性的貢獻(xiàn),它不但促使近代中國由一個(gè)松散的文化統(tǒng)一體(以“天下”為核心理念)轉(zhuǎn)變?yōu)楠?dú)立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以“政治主權(quán)”為主要特征),而且還為今天中國的富強(qiáng)打下來堅(jiān)實(shí)的思想基礎(chǔ)。沒有這一理念的支撐,任何花哨的理論和盲目的實(shí)踐對(duì)于中國人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
[32]
然而,問題在于,近代中國除了國家獨(dú)立以外,還有倡導(dǎo)科學(xué)、實(shí)行民主、厲行法治、實(shí)現(xiàn)憲政等諸多任務(wù),單一地強(qiáng)調(diào)國家獨(dú)立和富強(qiáng),將會(huì)降低甚至讓人忽視其他任務(wù)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或者將這些任務(wù)和價(jià)值僅僅看作是實(shí)現(xiàn)國家富強(qiáng)的手段。以法政領(lǐng)域?yàn)槔瑥那寮灸┢陂_始,中國人最初選擇的是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立憲”運(yùn)動(dòng)。當(dāng)時(shí)呼吁自由與民主,爭(zhēng)取憲政與法治一時(shí)蔚然成風(fēng)。然而。仔細(xì)回味這段歷史,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立憲的終極目標(biāo)并非是為了確保公民的權(quán)利與自由,而是試圖通過憲政提升公民的能力,最終達(dá)致國家富強(qiáng)。
[33]
誠如本杰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s,1964) 所觀察到地那樣,中國知識(shí)分子(以嚴(yán)復(fù)、梁?jiǎn)⒊瑸榇恚⿲?duì)于自由主義的渴求與他們追求國家富強(qiáng)的欲望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內(nèi)在緊張,一旦自由主義與國家富強(qiáng)之間發(fā)生矛盾,或者可以找到一條通往國家富強(qiáng)更便捷的道路,那么自由主義就必須讓路了;或者用李澤厚(1986)的話說,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中,救亡總是壓倒了啟蒙。1920年以后,中國人民(準(zhǔn)確地來說,主要是中國的精英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下拋棄自由主義開始追求馬克思主義就是對(duì)這種“捷徑”的選擇。
(二)國富民強(qiáng)、“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與土地公有制
按照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的說法,“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能夠成為20世紀(jì)中后期中國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本文并不想質(zhì)疑這一結(jié)論,而是希望探究“歷史”和“人民”為何要做出這樣的選擇,當(dāng)然,前提是我們假設(shè)它們是可以做出選擇的。
為此,我需要談及馬克思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理論以下兩個(gè)方面的特征: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古代“孔孟之道”一樣,追求公民德性,追求“共產(chǎn)主義”或者“世界大同”,并且對(duì)社會(huì)不公、私利、雄心以及物質(zhì)利益和肉欲快樂合法化進(jìn)行猛烈批判,這讓中國人對(duì)馬克思主義感到異常親切;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卻不像孔子或者盧梭那樣試圖回到遠(yuǎn)古的“黃金時(shí)代”,因而憎恨甚至詛咒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相反,他熱烈地?fù)肀切┰噲D通過“工程—技術(shù)方法”(engineering-technological approach)來實(shí)現(xiàn)理想社會(huì)的思想家(比如伏爾泰、百科全書派、圣西門等等),這讓中國人看到了國家富強(qiáng)和民族獨(dú)立的希望——因?yàn)樵隈R克思看來,現(xiàn)代工業(yè)和資本主義發(fā)展所帶來的剝削和社會(huì)不公確實(shí)應(yīng)當(dāng)受到最為猛烈的批判,但他又認(rèn)為這在“人類的歷史進(jìn)程中”是客觀的、進(jìn)步的和必須的,是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不可跨越的一個(gè)階段。他告誡人們,“物質(zhì)進(jìn)步是文化豐富的先決條件”,過了這一階段后,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工人階級(jí)將在資本主義的基礎(chǔ)之上建立起“物質(zhì)極大豐富”和“人們道德水平的極度高尚”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
理解上述兩個(gè)方面甚為重要,因?yàn)槠渲兴ǖ摹艾F(xiàn)代化”、“工業(yè)化”、“物質(zhì)豐富”和“道德高尚”等關(guān)鍵詞,不但是理解20世紀(jì)的中國為何最終選擇了“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的根本“命門”所在,而且實(shí)際上回答了為什么中國共產(chǎn)黨就一定要選擇土地公有制的原因。首先,在中國的精英們看來,只有社會(huì)主義的公有制,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技術(shù)和社會(huì)的快速發(fā)展,才能實(shí)現(xiàn)國家的富強(qiáng);其次,只有實(shí)行生產(chǎn)資料的公有制,數(shù)千年來中國老百姓嚴(yán)重的貧富差距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數(shù)千年來中國人的自私自利習(xí)性才能在國家和集體的“懷抱”中逐漸被消滅,最終才能成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社會(huì)主義新人,而到那時(shí),共產(chǎn)主義就將降臨中國大地。
[34]
當(dāng)然,這里存在一個(gè)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無論是在地球上哪一個(gè)國家,如果說國家或者民族的獨(dú)立是關(guān)乎所有人的事情,那么所謂“國家富強(qiáng)”對(duì)于普通民眾來說,通常就過于遙遠(yuǎn)了,他們更多地關(guān)注自己的生活,關(guān)心自己的財(cái)產(chǎn),而沒有精力,也沒有興趣關(guān)注這么宏偉的事情。那為何數(shù)千年來生活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土地私有”之下的中國民眾會(huì)接受精英們所追求塑造的“國家富強(qiáng)”的愿景和“一大二公”的理想呢?這就需要強(qiáng)調(diào)意識(shí)形態(tài)的“誘導(dǎo)”和“規(guī)制”功能——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1981)曾提到,意識(shí)形態(tài)有三種功能,我在這里強(qiáng)調(diào)的,大致相當(dāng)于其所強(qiáng)調(diào)的前兩種功能。
[35]
我在上文中已經(jīng)說明,中國農(nóng)民之所以參加革命主要是為了獲得土地所有權(quán),這一點(diǎn)應(yīng)該得到承認(rèn)和堅(jiān)持的。不過上述的結(jié)論是否意味著,中國農(nóng)民因此就反對(duì)彼此之間的互助或者合作?并且反對(duì)彼此在互助和合作基礎(chǔ)之上的共同富裕呢?很顯然,這兩個(gè)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事實(shí)上,中國農(nóng)民并不反對(duì)互助合作和共同富裕,只是不曾找到實(shí)現(xiàn)這一理想的合適道路而已,所以不得不在“昌盛(地主)-衰敗(農(nóng)民)”地惡性循環(huán)中彼此競(jìng)爭(zhēng),自然村落也不得不如同日月、四季和生死的循環(huán)一樣,在數(shù)以千年計(jì)地歷史長河中,上演著情節(jié)大致相似的悲歡離合故事。
據(jù)說,如果不是受到列強(qiáng)的入侵,明清時(shí)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就能夠順利地發(fā)展,中國農(nóng)民也可以走向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道路,但這終究只是一種假設(shè),既無法證實(shí),也不曾實(shí)現(xiàn)。于是,當(dāng)有一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宣布通過“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理論,中國人可以找到一種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的道路時(shí),這對(duì)中國農(nóng)民來說都是極具誘惑和吸引力的,他們猶豫、懷疑、害怕,但又充滿憧憬,最終在意識(shí)形態(tài)的誘導(dǎo)和動(dòng)員下,像剛剛生育的媽媽要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托兒所一樣,在復(fù)雜迷亂的情緒中,紛紛交出剛剛拿到手的土地證。
當(dāng)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會(huì)在猶豫中接受意識(shí)形態(tài)的誘導(dǎo),或者“隨大流”。特別是對(duì)于那些是經(jīng)由數(shù)代辛勤勞作而獲得土地的農(nóng)民,以及那些剛剛因?yàn)楦锩鼊倮@得土地的貧農(nóng)和雇農(nóng)來說,讓他們主動(dòng)將自己的土地交給集體簡(jiǎn)直是“革”他們的命。對(duì)于前者來說,交出土地相當(dāng)于自毀家業(yè),愧對(duì)祖先;而對(duì)后者來說,相當(dāng)于別人許諾給他一個(gè)禮物以換取他的支持和奉獻(xiàn),但是任務(wù)完成后,剛剛拿到手還沒有看上幾眼,這一禮物卻又被收回去了,那種失落和憤怒自然會(huì)十分強(qiáng)烈。
[36]這時(shí),意識(shí)形態(tài)的“規(guī)制”功能就發(fā)揮效果了,不過,這次是藉由“盧梭-馬克思”的“汝不自由,迫使汝自由”的名義,
[37]依靠強(qiáng)大的國家機(jī)器,農(nóng)民以及農(nóng)民組織對(duì)于政權(quán)的依附性,以及“土改形成的農(nóng)民私有權(quán)并不穩(wěn)固”(周其仁,1994)來實(shí)現(xiàn)的。
[38]
(三)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壓力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修正
意識(shí)形態(tài)不是無所不能的,“誘導(dǎo)”和“規(guī)制”功能的發(fā)揮也不是毫無條件的。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1981)曾說,
當(dāng)人們的經(jīng)驗(yàn)與其意識(shí)形態(tài)不相吻合時(shí),他們就會(huì)改變其意識(shí)形態(tài)觀點(diǎn),不過……只有在長久的變化有悖于個(gè)人的理性或根本改變個(gè)人的福祉時(shí),人們才會(huì)去改變其意識(shí)形態(tài)。
1930年代,中國共產(chǎn)黨在經(jīng)歷了數(shù)十年的奮斗后,發(fā)現(xiàn)中國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和生活在其中的民眾并不接受“土地公有制”,于是不得不修正自身的意識(shí)形態(tài),宣布“地權(quán)歸農(nóng)”,由此取得了人民的擁護(hù),并完成了實(shí)現(xiàn)國家獨(dú)立的偉大使命。
1950年代,當(dāng)這個(gè)積貧積弱、工業(yè)基礎(chǔ)薄弱卻又躊躇滿志、雄心勃勃的國家希望迅速實(shí)現(xiàn)第二大任務(wù)即“國家富強(qiáng)”時(shí),它又重新豎起“土地公有制”的大旗,只不過這次意識(shí)形態(tài)的變革是與理想的再次高昂有關(guān),而與過往的經(jīng)驗(yàn)無關(guān)。期間所進(jìn)行的農(nóng)村社會(huì)主義改造運(yùn)動(dòng),既是為了改變千年以來松散的以家庭為基本生產(chǎn)單位的傳統(tǒng)生產(chǎn)方式,提供更高生產(chǎn)效率且更加有利于社會(huì)公平的新的組織形式,也是為了更多地把農(nóng)業(yè)剩余轉(zhuǎn)化為工業(yè)化積累,完成國家的強(qiáng)大所必須的“資本原始積累”。“人定勝天”的口號(hào)可能是這個(gè)時(shí)期最鮮明的標(biāo)志,卻也暗藏了其失敗的必然命運(yùn)。
1970年代末期,當(dāng)人民公社體制許諾給人們的美好生活演變?yōu)槿諒?fù)一日的穩(wěn)定貧困時(shí),殘酷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終于使那些曾經(jīng)癡迷于人民公社體制的人們開始行動(dòng)起來,修改他們關(guān)于“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先是安徽省小崗村,18個(gè)農(nóng)民冒著被殺頭的危險(xiǎn),以“18個(gè)血手印”沖垮輝煌一時(shí)的人民公社,并開啟了后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隨后中共內(nèi)部就如何看待這一“誘發(fā)性制度變遷”以及其背后所蘊(yùn)含的意識(shí)形態(tài)變化發(fā)生了激烈的爭(zhēng)論。爭(zhēng)論的結(jié)果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被迫做出修正,農(nóng)民都是或者都應(yīng)是“大公無私”的人性假設(shè)不得不被放棄,執(zhí)政黨也開始以一種實(shí)用主義的態(tài)度看待馬克思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不但承認(rèn) “自私、追求財(cái)富是人的天性”,而且努力回避意識(shí)形態(tài)的爭(zhēng)論,將發(fā)展經(jīng)濟(jì)作為自己的第一要?jiǎng)?wù)。由此,公民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渴望因此得到釋放,社會(huì)也因此獲得極大發(fā)展和繁榮。
(四)意識(shí)形態(tài)變遷與中國土地制度中的“權(quán)利-義務(wù)”變化
社會(huì)理論大師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1995)在他著名的社會(huì)系統(tǒng)理論中認(rèn)為,伴隨著人類社會(huì)復(fù)雜性的持續(xù)增長,人類歷史演化經(jīng)由“分割”時(shí)代和“分層”時(shí)代,現(xiàn)在已經(jīng)進(jìn)入“功能分化”時(shí)代,即社會(huì)分為政治、經(jīng)濟(jì)、法律、宗教以及藝術(shù)等等領(lǐng)域,不同的社會(huì)系統(tǒng)通過溝通媒介、二元編碼和系統(tǒng)項(xiàng)目,一方面進(jìn)行自我編碼且彼此獨(dú)立運(yùn)作,比如政治領(lǐng)域的溝通媒介是“權(quán)力”,二元編碼是有權(quán)/無權(quán),系統(tǒng)項(xiàng)目是議會(huì)、政府和民主機(jī)制;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的溝通媒介是“貨幣”,二元編碼是有貨幣/無貨幣(或是投資/不投資),系統(tǒng)項(xiàng)目是市場(chǎng)、價(jià)格信號(hào)與購買銷售;而法律領(lǐng)域的溝通媒介是“法”(權(quán)利-義務(wù))本身,二元編碼是合法/違法,系統(tǒng)項(xiàng)目是實(shí)證法(復(fù)雜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則通過“溝通”(communications)與周圍的環(huán)境(由其他系統(tǒng)組成)進(jìn)行意義連接,從而實(shí)現(xiàn)系統(tǒng)間的彼此協(xié)調(diào)和耦合和社會(huì)的有效運(yùn)作。
然而,20世紀(jì)的中國似乎并沒有實(shí)現(xiàn)從“階層分化”向“功能分化”的完全轉(zhuǎn)變,以至于出現(xiàn)了意識(shí)形態(tài)統(tǒng)領(lǐng)下的編碼互相侵入、邊界互相交叉,功能相互紊亂的“怪現(xiàn)狀”:藝術(shù)不用自己編碼“美/不美”,而是用 “政治正確”作為評(píng)價(jià)的標(biāo)準(zhǔn);經(jīng)濟(jì)不是用“貨幣/無貨幣”而是以“是否符合國家權(quán)力意志”來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法律也不是法律,因?yàn)閺?qiáng)調(diào)“階級(jí)斗爭(zhēng)”和“生產(chǎn)資料歸誰所有”的政治和經(jīng)濟(jì)標(biāo)準(zhǔn),不但不排擠了法律自身的溝通媒介和二元編碼,而且還曾一度直接取消了這一系統(tǒng),文革期間用“政策代替法律”以及砸爛公檢法的瘋狂運(yùn)動(dòng)就是例證。
具體到財(cái)產(chǎn)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法律系統(tǒng)溝通媒介和二元編碼的紊亂表現(xiàn)在,分析某一財(cái)產(chǎn)制度屬于“公有”還是“私有”的邏輯和標(biāo)準(zhǔn)不是法律的“權(quán)利-義務(wù)”,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所強(qiáng)調(diào)的“生產(chǎn)資料歸誰占有”——擁有數(shù)以百萬計(jì)甚至千萬計(jì)股東的現(xiàn)代股份上市公司仍然是財(cái)產(chǎn)私有制,是因?yàn)樯a(chǎn)資料主要被資本家占有;而盡管只有數(shù)千人甚至數(shù)百人、數(shù)十人的農(nóng)民集體之所以是“公有制”,是因?yàn)樗纳a(chǎn)資料被該集體內(nèi)全體農(nóng)民占有。人們常常疑惑于 “集體所有”往往不過是區(qū)區(qū)幾百人甚至幾十人所有,為何在中國被看作是“公有制”而非“私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shí)答案就在這里,而今天中國出現(xiàn)農(nóng)村土地所有者無法確認(rèn)也與此一編碼錯(cuò)位密切相關(guān)。
甚為遺憾的是,包括憲法(2004)和物權(quán)法(2007)等在內(nèi)的中國法律至今沒有意識(shí)到這一問題,依然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關(guān)于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作為衡量土地等財(cái)產(chǎn)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的標(biāo)準(zhǔn),這既表明了在中國進(jìn)行改革的艱難,也讓我們看到了未來中國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變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