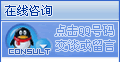正文
2009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下簡稱IMF)宣布對現行貸款框架進行“大修”,其主要內容包括:新增“靈活貸款安排”(Flexible Credit Line,FCL),以取代現行的“短期流動性機制”(Short- Term Liquidity Facility,SLF);繼續簡化事后條件性貸款( ex - post conditionality)的貸款條件,提高貸款的靈活度和可獲得性;將非優惠貸款上限提高一倍;調整和簡化貸款成本及到期償付結構;放松對低收入國家優惠貸款的審批條件;停止一些“無人問津”的貸款工具等。 [1]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FCL的引入。FCL作為事前條件性貸款的一種,其具體適用范圍是什么,與過去實施的事前條件性貸款項目有何區別,與事后條件性貸款的關系是什么,對IMF貸款框架未來的發展又會有何影響,這都是伴隨此次改革所產生的問題。本文將從事前條件性貸款在IMF中的歷史出發,并對現有的理論模式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對FCL與之前實施的事前條件性貸款項目進行比較,進一步明確FCL的特點以及事前條件性貸款在實踐中的發展趨勢;最后,文章將對本次改革進行評析,并從事前條件性貸款的角度,對IMF貸款項目框架未來改革的走向提出一點看法。
一、歷史回顧
在IMF的歷史上,事前條件性貸款并非一個新生的概念。事實上,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IMF最初引入條件性貸款時,其本意就是事前性的。這是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各成員國無法隨意調整經常項目下的支付,也不能在未經IMF同意的情況下改變匯率,各國匯率也就得以保持相對穩定,避免了國際資本流動引發的匯率風險。當時,IMF的條件性貸款主要是為了促使各國調整政策,解決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以穩定幣值,防范危機的發生。
條件性貸款從事前預防轉移至事后救助是伴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而發生的。釘住匯率制(Pegged Exchange Rate)的崩壞和自由匯率制(Free Exchange Rate)的確立活躍了國際資本市場,卻也增加了匯率風險,危機頻頻發生。20世紀七八十年代,IMF大量使用事后條件性貸款以救助遭受危機的國家。雖然當時也有聲音指出,IMF資金的保險效應可能引發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 [2] 因此應以事前條件性貸款取代事后條件性貸款,拒絕非危機時期經濟政策不利的國家在發生危機后的貸款要求, [3] 但IMF的主流觀點仍堅持事后貸款不會引發道德風險,并未將事前條件性貸款納入貸款框架。
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金融危機使IMF資金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理論界提出,IMF應要求申請貸款的國家達到事前設定的條件,拒絕不符合條件的國家的貸款要求(或減少貸款發放的數額)。經過深入的討論,IMF于1999年設立了一個新的貸款項目,即臨時貸款安排(Contingent Credit Line)。這一項目專門針對經濟政策良好,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傳染性可能受到波及的國家。這些國家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可以向IMF申請短期貸款,以防止受到危機的影響。IMF通過批準貸款,可表達對該國經濟政策的認同,促使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該國。但是,該項目并沒有規定具體的事前條件,也沒有對當時其他的貸款項目作出任何改變。在其實施的5年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使用過此項貸款。2003年,該項目自動失效。
在此后的幾年中,理論界對事前條件性貸款的其他可能性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討論。部分學者設計了新型的事前條件性貸款項目, [4] 也有學者提出通過與IMF監督制度(Surveillance)的結合將事前條件引入所有的貸款項目 [5] 。近兩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將事前條件性貸款這一課題又一次提上桌面。IMF于2009年3月出臺的靈活貸款安排正是IMF對事前條件性貸款的一次新的嘗試。截至2010年4月,已有墨西哥、哥倫比亞、波蘭三國向IMF提出了該項下的貸款申請,并已經獲得了批準。
二、理論基礎
自從事后條件性貸款項目的各種缺陷逐漸暴露后,理論界開始從各個角度探索事前條件性貸款所可能采取的框架。以事前條件性貸款與事后條件性貸款的關系為標準,現有的理論模型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前者作為后者補充的互補型模式,另一類是以前者取代后者的替代型模式。
互補型模式的基本前提是傳統的事后條件在一般情況下并不會引起道德風險。雖然IMF的貸款可能削弱國家進行事前防御措施的動機,但國家出于事前防御可以減少損失和事后防御成本的考慮,并不一定會怠于采取事前措施。即使國家真的冒險選擇減少事前防御,這也可以視為IMF“定心丸”作用在非危機時期的體現,并不會影響國際社會的整體福利。但是,當單個國家的經濟危機具有外部性,或該國的政治體制導致政府意志并不能有效反映社會意志時,IMF的事后條件性貸款就可能引發道德風險。這是因為,若危機具有蔓延至他國的可能性,原發國進行事前防御的果實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國所享用,而政府由于其任期有限,采取防御措施的當屆政府也未必能嘗到降低事后成本的甜頭。在這兩種情況下,國家由于自私或短視,可能更傾向于不進行事前防御。主張互補型模式的學者認為,IMF通過采用事前貸款性條件可以對政府的動機產生影響,從而抵消在這兩種情形下可能發生的道德風險,使政府更傾向于進行事前防御。但根據其基本前提,即存在這兩種情形的危機的國家只是少數,在大部分情形下,并不需要啟用事前貸款性條件。因此,在IMF的危機貸款中,事后條件仍應是原則,只有在少數可能發生道德風險的情況下才需要使用事前條件。 [6]
與互補型模式相對,以Axel Dreher為代表的部分學者主張事后條件性貸款應完全由事前條件性貸款取代。這一模式建立在全盤否定IMF事后條件性貸款有效性的基礎之上。 [7] 根據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事后條件性貸款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貸款條件可以對陷入危機的國家在危機發生后轉變經濟政策起到保證作用(Commitment Effect)。如果借款國內部各個利益團體之間所贊同的經濟政策趨于一致,并且與IMF所推崇的政策相同,貸款條件可以通過保證借款國在取得貸款后對這些政策的落實,以獲取潛在貸款主體的信任,從而在危機擴大之前就獲得足夠的資金以解決“債務懸垂” ( Debt Overhung)問題。 [8] 即使借款國內部對“正確的”經濟政策并未達成共識,貸款性條件也可以加重與IMF觀點一致一方的籌碼,提高借款國轉變經濟政策的可能性。 [9] 在這一理論模型下,貸款條件能夠得以執行是其保證作用實現的前提。可惜的是,現有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無論采取何種統計方法,貸款條件的執行水平都是相對低下的。 [10]
二是“賄賂政府”(Bribing the Government), [11] 即以發放貸款為條件,誘使借款國采取其原本并不贊同的經濟政策。IMF認為,采取正確的(即IMF所認同的)經濟政策是保證貸款能夠得以償還的必然要求。只有通過貸款條件的執行,改變借款國原有的經濟方針,才能保證其有能力償還貸款,使IMF其他成員國的利益不受到損害。同樣,這一理論的成立也是建立在貸款條件能夠得以良好執行的假設之上。而正如上文所述,此假設在現實中很難成立。即使條件得以執行,由于其與借款國的本意背道而馳,這一執行也常常只是暫時的,等危機過后或貸款償還后,借款國又還原至原有的經濟政策。此外,IMF所贊同的政策是否一定正確,這一問題本身就沒有明確的答案。事實上,大量的數據顯示,IMF在危機中開出的“藥方”常常過急或過猛,不僅未能救危機中的借款國于水火之中,反而可能起到加劇危機的反作用。 [12]
三是其“信號作用”(Signal Effect)。 [13] IMF可以從貸款條件中窺探潛在借款國的經濟政策方針,以篩選出政府能力強且政策穩健的國家投放貸款。同時,IMF的貸款條件也可以對其他貸款主體起到信號作用,使其更傾向于向獲得IMF條件性貸款的國家發放貸款。但在現實中,危機的緊迫性和嚴重性使IMF在發放貸款時對貸款投向國幾乎不加選擇。而由于條件設定的本身深受IMF的影響,也很難反映出借款國政府的真實意愿。 [14] 事后條件性貸款的信號作用在實踐中的效果不得不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四是其對“道德風險”的規避作用。條件的設定提高了借款國的借款成本,從而增強了各國在危機前采取防御措施的動機,減少了其因仰仗IMF的救助而怠于防御的可能性。但若IMF的條件只是擺設,無論條件是否得以執行,下一期的貸款仍會發放,借款國的動機就不會受到影響。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事實正是如此:IMF出于各種考慮,即使條件未得以執行,仍會選擇發放下一期貸款, [15] 這也就使得貸款條件理論上的規避作用在現實中難以實現。
鑒于實證研究的數據幾乎否定了貸款條件所有在理論上的作用,Dreher對貸款條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廢除現有的事后條件制度,以事前條件制度取而代之。
根據Dreher的模型,IMF應在非危機時期對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情況進行評估,并定期公開評估報告。危機時期各國所能獲得的貸款的數額和利率應根據其日常的經濟政策水平而定,二者如何掛鉤的標準也應在非危機時期予以公開。這樣,各國就會產生足夠的動機改善日常的經濟政策,并且可以避免事后條件的制約。
三、實踐中的運用
(一)臨時貸款安排(Contingent Credit Line,CCL)
IMF于1999年出臺的CCL是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事前條件性貸款項目。在該項目下取得貸款需通過資格審批和貸款啟動兩個階段。
IMF首先對申請國經濟政策的各方面進行評估,作出其是否有資格獲得貸款的決定,進而在申請國受到經濟危機波及而產生資金需要時進行貸款啟動的審核,以決定是否發放貸款。IMF希望通過該項目的實施,保證實施穩健經濟政策的國家在受到來自外部的經濟危機的波及時,能夠有足夠的資金渡過難關,并間接鼓勵各國采取更穩健的經濟政策和危機防范措施。 [16]
CCL與IMF的其他貸款項目不同:它以事前條件,即對借款國經濟政策的評估替代包括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各種事后條件;在申請該項目貸款時,申請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必須良好,不得有對資金的現實需要;且該項目只適用于受到金融危機傳染效應影響的國家,不包括危機原發國。從這個角度而言,CCL更接近于互補型模式,即事前條件性貸款只在特殊情況下使用,而并不適用于危機不具有外部傳染性,發生道德風險可能性較小的情況。
CCL在生效的5年內未被任何國家使用過,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非危機時期向IMF申請CCL項下的貸款,可能會給市場帶來經濟形勢惡化的錯覺,從而動搖市場信心,對該國的資本市場產生不利影響。若在取得CCL貸款后喪失資格,又可能給市場造成該國經濟政策出現問題的印象,同樣可能對資本市場產生負面影響。這就使申請國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無論是進是退,都有對市場信心產生不良影響的可能。二是CCL并未對申請國的貸款資格設置具體的標準,貸款資格的確定因而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其客觀性和公正性也更容易受到質疑。三是獲得貸款需要經歷資格審批和貸款啟動兩個階段,即使取得了貸款資格,也未必能夠獲得貸款。這一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不少國家望而卻步。四是CCL只適用來源于外部的傳染性危機,而在現實中,危機往往同時存在于經常項目下和資本項目下,并同時受到內部與外部的影響,很難嚴格區分。 [17]
CCL所存在的這些問題說明,一方面,事前性條件貸款由于其“信號作用”,可能對資本市場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有些影響甚至會與貸款項目的初衷背道而馳。事前條件性雖然避免了事后條件中最受詬病的結構性條件,卻因為難以對條件進行細化和量化,影響了條件的客觀性。另一方面,以是否具有外部性為標準對經濟危機進行區分在理論上或許很有吸引力,在現實中卻難以實現。倘若將事前條件性貸款僅僅限制在具有外部性的危機之內,可能使潛在申請國由于無法確定危機的類型而放棄提出貸款要求,也給IMF判斷具體情形是否屬于貸款項目的范圍加大了難度。
(二)靈活貸款安排(FCL)
IMF于2009年出臺的靈活貸款安排是事前條件性貸款的一次新嘗試。它取代了2008年出臺的SLF,取消了貸款上限,延長了貸款償付期間,并將適用范圍由危機處理擴大到危機防范和處理兩個階段。與CCL相同,此貸款項目不設任何事后性條件,而是以各國的經濟政策水平為標準,決定是否發放貸款。但與CCL相比,FCL又具有一些新特點:一是與CCL要求申請貸款時沒有危機迫近不同,FCL下的貸款可以在危機發生時申請,也可以作為預防性措施,在非危機時期申請。二是FCL的使用并不限于具有外部傳染性的危機,而是適用于任何類型的金融危機。三是FCL對國家經濟政策水平的審查以該國的貸款申請為前提,且在確定發放貸款之前嚴格向外界保密。相反,在CCL下,IMF在收到貸款申請之前就可能對潛在貸款國的政策狀況進行評估,且對是否將結果保密并無明確規定。四是FCL詳細規定了經濟政策水平的評估標準,但不對標準進行絕對量化,而是在綜合考慮各項因素的基礎之上作出最終評價。 [18]
FCL的這些新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CCL之前存在的問題。首先,貸款申請的保密性避免了其對市場的“信號效應”,使市場信心不會因為貸款申請和退出本身受到影響,從而打消了潛在申請國最大的顧慮。其次,FCL不要求對危機的類型作出明確判斷,IMF作出貸款決定的難度也就隨之降低。最后,明確的評估標準便于潛在申請國更準確地估計本國經濟政策水平,使其能夠更有的放矢地作出是否申請貸款的決定。對其他市場主體而言,也能更明確IMF同意或者拒絕貸款決定的原因,從而避免盲目行為,維持資本市場的穩定。與CCL遭到的冷遇不同,FCL出臺不到半年,就已經收到了包括墨西哥等三國的貸款申請。雖然不能否認金融危機這一客觀要素對各國資金需求的影響,但FCL的受歡迎程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其在現實中的可行性。
從設計結構上看,FCL更類似于Dreher所提出的模型,即將事前條件性貸款普遍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危機,且既可用于危機處理,又可用于危機防御。但從實質上看,FCL與Dreher的模型又有著根本的區別:在Dreher的模型下,事后條件性貸款應徹底為事前條件性貸款所取代,事前條件適用于所有成員國,并以事前條件為確定貸款數額和利率的主要標準。而FCL作為一個新型貸款項目,與傳統的事后條件性貸款項目并存,且由于申請資格的標準嚴格,能夠符合申請條件的國家也非常有限。從這個角度看,FCL仍是作為傳統事后條件性貸款的補充而非替代而存在的。
四、對本次貸款項目改革的評析
IMF在本次改革中出臺的FCL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都超越了之前的CCL,這說明IMF開始更為積極地使用事前條件性貸款這一貸款模式。但正如上文所述,FCL可適用的范圍相對有限,可見IMF并不愿貿然將事前條件性貸款鋪開,更遠未達到以其替代事后條件性貸款的地步。
IMF的謹慎可能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事前條件性貸款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不成熟性。首先,事前條件性貸款所設立的審查標準應包括哪些方面,各方面在最終決定上又應占到多大比重,這些都需要有成熟的經濟學理論作為支撐。事前條件性貸款將這些標準與各國所能獲得的貸款數額直接掛鉤,其與各國的利益相關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設置套具有足夠說服力的標準,事前條件性貸款的公正性與科學性也必然遭受公眾的質疑。另外,隨著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普適性逐漸遭到越來越多的懷疑。什么是真正“好的”經濟政策,這一問題的答案也越來越不確定。在這種情況下,由一套IMF自己設定的標準決定各國的命運,其合理性和正當性也自然需要更充分的論證。
其次,非危機時期對各國經濟政策的評估會對資本市場產生何種影響也需要進一步研究。雖然FCL通過對審查階段的保密緩解了各國對信號效應的顧慮,但如果事前條件性貸款擴大適用于所有成員國,保密也就不再具有可能性。如果按照Dreher的模型,將對各國的評估結果完全公開,其對市場影響的不確定性也會進一步增加。在深入研究結果出來之前,任何貿然的措施都有可能重蹈CCL的覆轍。
再次,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在危機發生后,即使成員國根據事前條件并不具備貸款資格,IMF也很難拒絕其要求。一方面,由于經濟危機的直接受害者是各國國民,而IMF很難置民眾的利益與國家社會的壓力于不顧。另一方面,IMF對各國經濟政策的監督和指導作用建立在與其長期合作關系的基礎之上。如果IMF在成員國危急時刻見死不救,則必然會對這一長期關系的延續產生不利的影響。當然,如果IMF只是減少貸款的數額,而非徹底拒絕提供貸款,是否能夠避免這些因素的作用,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19]
此外,雖然有大量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否附加貸款條件,借款國最終都會歸還IMF貸款, [20] 但以事前條件徹底替代事后條件,并適用于所有的成員國,其風險仍不容小覷。這也可能是IMF采取保守改革態度的原因之一。出于以上種種考慮,IMF僅對有限范圍內的國家適用事前條件性貸款也就不難理解了。
此次改革,IMF雙管齊下,一方面引入事前條件性貸款,另一方面繼續深化對事后條件性貸款的改革。
此舉看似砍柴磨刀兩不誤,但在筆者看來卻并非一勞永逸之舉。這是因為,FCL的高門檻意味著其只可能適用于少數經濟實力較強的新興國家,而眾多不發達國家則被拒之門外。這些國家經濟落后,經濟政策水平也相對低下,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達到取得FCL貸款申請資格所需的標準。事前條件性貸款的改革和FCL的引入對這些國家來說幾乎毫無意義,它們所能夠取得的貸款仍只有附帶結構性條件的傳統事后性貸款。IMF的改革既不能為它們帶來更多的資源,也不能起到鼓勵它們加強事前防御的作用。相反,IMF的公平性可能因此而從根本上遭到質疑。FCL的引入造成了差別待遇的客觀效果:經濟實力較強,經濟政策符合IMF評價標準的國家可以選擇事前條件性貸款在危機發生前就進行防范,且無須作出改變經濟政策的保證;而經濟實力較弱,經濟政策與“正統”標準不一致的國家則只能坐以待斃,并被迫接受可能包括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嚴苛的事后條件。如果說,過去國際社會對IMF采取雙重標準的批評還只是停留在個案上,FCL的局部適用將使這一批評擴大到IMF貸款框架的整體。 [21]
此外,根據FCL的設計,IMF對申請國貸款資格的評定建立在綜合考慮各項標準的基礎之上,從客觀上擴大了IMF的自主裁量權。且這一評價過程幾乎全程對外保密,IMF的決定因而更容易受到來自強權的影響。FCL出臺后,亞洲國家的反應一直較為冷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部分國家對于IMF仍持懷疑態度。
IMF若長期只在部分國家中適用事前條件性貸款,而對其他國家仍適用事后條件性貸款,勢必從根本上危及其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公平性。有鑒于此,筆者認為,IMF應將本次改革作為一次過渡,將FCL作為一個試驗性的貸款工具,根據其實施效果確定下一步改革的走向。倘若效果良好,則總結經驗,將事前條件性貸款擴大至所有成員;以統一的標準對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情況進行評估,并將評估結果與貸款數額和利率等掛鉤。這一評估可以與IMF現有的監督機制(Surveillance)相結合,也可以另起爐灶,建立新的評估機制。關鍵是,該評估須在所有成員國中進行,而非如目前FCL所實行的,僅以申請為前提在個別國家中進行。
五、結語
事前條件性貸款從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危機中孕育而生,從最初只適用于外部性危機的CCL,到2009年出臺的適用于所有危機類型,且既可用于危機防范又可用于危機解決的FCL,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理論界關于事前條件性貸款的原理,其與事后條件性貸款的關系,以及可能采取的形式等各種討論也從未間斷。從總的趨勢上看,事前條件性貸款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大,其內容設計也越來越成熟。隨著各國對事前條件性貸款了解的深入,敢于“吃螃蟹”的國家也越來越多。但是,目前的事前條件性貸款仍是作為事后條件性貸款的補充而存在的,其所采用的申請制和設置的高標準使其適用范圍受到了嚴格限制,從客觀上導致了對經濟實力和經濟政策水平不同的國家的差別對待。因此,FCL不可能長期存在,而應視為IMF對貸款項目深化改革的前奏。下一步的改革是前進(將事前條件性貸款在成員國中全面鋪開),還是后退(取消事前條件性貸款,仍沿用傳統的事后條件性貸款,只是對條件的具體內容進行改良),有待對FCL實施效果的進一步觀察。
一、歷史回顧
在IMF的歷史上,事前條件性貸款并非一個新生的概念。事實上,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IMF最初引入條件性貸款時,其本意就是事前性的。這是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各成員國無法隨意調整經常項目下的支付,也不能在未經IMF同意的情況下改變匯率,各國匯率也就得以保持相對穩定,避免了國際資本流動引發的匯率風險。當時,IMF的條件性貸款主要是為了促使各國調整政策,解決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以穩定幣值,防范危機的發生。
條件性貸款從事前預防轉移至事后救助是伴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而發生的。釘住匯率制(Pegged Exchange Rate)的崩壞和自由匯率制(Free Exchange Rate)的確立活躍了國際資本市場,卻也增加了匯率風險,危機頻頻發生。20世紀七八十年代,IMF大量使用事后條件性貸款以救助遭受危機的國家。雖然當時也有聲音指出,IMF資金的保險效應可能引發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 [2] 因此應以事前條件性貸款取代事后條件性貸款,拒絕非危機時期經濟政策不利的國家在發生危機后的貸款要求, [3] 但IMF的主流觀點仍堅持事后貸款不會引發道德風險,并未將事前條件性貸款納入貸款框架。
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金融危機使IMF資金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理論界提出,IMF應要求申請貸款的國家達到事前設定的條件,拒絕不符合條件的國家的貸款要求(或減少貸款發放的數額)。經過深入的討論,IMF于1999年設立了一個新的貸款項目,即臨時貸款安排(Contingent Credit Line)。這一項目專門針對經濟政策良好,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傳染性可能受到波及的國家。這些國家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可以向IMF申請短期貸款,以防止受到危機的影響。IMF通過批準貸款,可表達對該國經濟政策的認同,促使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該國。但是,該項目并沒有規定具體的事前條件,也沒有對當時其他的貸款項目作出任何改變。在其實施的5年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使用過此項貸款。2003年,該項目自動失效。
在此后的幾年中,理論界對事前條件性貸款的其他可能性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討論。部分學者設計了新型的事前條件性貸款項目, [4] 也有學者提出通過與IMF監督制度(Surveillance)的結合將事前條件引入所有的貸款項目 [5] 。近兩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將事前條件性貸款這一課題又一次提上桌面。IMF于2009年3月出臺的靈活貸款安排正是IMF對事前條件性貸款的一次新的嘗試。截至2010年4月,已有墨西哥、哥倫比亞、波蘭三國向IMF提出了該項下的貸款申請,并已經獲得了批準。
二、理論基礎
自從事后條件性貸款項目的各種缺陷逐漸暴露后,理論界開始從各個角度探索事前條件性貸款所可能采取的框架。以事前條件性貸款與事后條件性貸款的關系為標準,現有的理論模型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前者作為后者補充的互補型模式,另一類是以前者取代后者的替代型模式。
互補型模式的基本前提是傳統的事后條件在一般情況下并不會引起道德風險。雖然IMF的貸款可能削弱國家進行事前防御措施的動機,但國家出于事前防御可以減少損失和事后防御成本的考慮,并不一定會怠于采取事前措施。即使國家真的冒險選擇減少事前防御,這也可以視為IMF“定心丸”作用在非危機時期的體現,并不會影響國際社會的整體福利。但是,當單個國家的經濟危機具有外部性,或該國的政治體制導致政府意志并不能有效反映社會意志時,IMF的事后條件性貸款就可能引發道德風險。這是因為,若危機具有蔓延至他國的可能性,原發國進行事前防御的果實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國所享用,而政府由于其任期有限,采取防御措施的當屆政府也未必能嘗到降低事后成本的甜頭。在這兩種情況下,國家由于自私或短視,可能更傾向于不進行事前防御。主張互補型模式的學者認為,IMF通過采用事前貸款性條件可以對政府的動機產生影響,從而抵消在這兩種情形下可能發生的道德風險,使政府更傾向于進行事前防御。但根據其基本前提,即存在這兩種情形的危機的國家只是少數,在大部分情形下,并不需要啟用事前貸款性條件。因此,在IMF的危機貸款中,事后條件仍應是原則,只有在少數可能發生道德風險的情況下才需要使用事前條件。 [6]
與互補型模式相對,以Axel Dreher為代表的部分學者主張事后條件性貸款應完全由事前條件性貸款取代。這一模式建立在全盤否定IMF事后條件性貸款有效性的基礎之上。 [7] 根據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事后條件性貸款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貸款條件可以對陷入危機的國家在危機發生后轉變經濟政策起到保證作用(Commitment Effect)。如果借款國內部各個利益團體之間所贊同的經濟政策趨于一致,并且與IMF所推崇的政策相同,貸款條件可以通過保證借款國在取得貸款后對這些政策的落實,以獲取潛在貸款主體的信任,從而在危機擴大之前就獲得足夠的資金以解決“債務懸垂” ( Debt Overhung)問題。 [8] 即使借款國內部對“正確的”經濟政策并未達成共識,貸款性條件也可以加重與IMF觀點一致一方的籌碼,提高借款國轉變經濟政策的可能性。 [9] 在這一理論模型下,貸款條件能夠得以執行是其保證作用實現的前提。可惜的是,現有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無論采取何種統計方法,貸款條件的執行水平都是相對低下的。 [10]
二是“賄賂政府”(Bribing the Government), [11] 即以發放貸款為條件,誘使借款國采取其原本并不贊同的經濟政策。IMF認為,采取正確的(即IMF所認同的)經濟政策是保證貸款能夠得以償還的必然要求。只有通過貸款條件的執行,改變借款國原有的經濟方針,才能保證其有能力償還貸款,使IMF其他成員國的利益不受到損害。同樣,這一理論的成立也是建立在貸款條件能夠得以良好執行的假設之上。而正如上文所述,此假設在現實中很難成立。即使條件得以執行,由于其與借款國的本意背道而馳,這一執行也常常只是暫時的,等危機過后或貸款償還后,借款國又還原至原有的經濟政策。此外,IMF所贊同的政策是否一定正確,這一問題本身就沒有明確的答案。事實上,大量的數據顯示,IMF在危機中開出的“藥方”常常過急或過猛,不僅未能救危機中的借款國于水火之中,反而可能起到加劇危機的反作用。 [12]
三是其“信號作用”(Signal Effect)。 [13] IMF可以從貸款條件中窺探潛在借款國的經濟政策方針,以篩選出政府能力強且政策穩健的國家投放貸款。同時,IMF的貸款條件也可以對其他貸款主體起到信號作用,使其更傾向于向獲得IMF條件性貸款的國家發放貸款。但在現實中,危機的緊迫性和嚴重性使IMF在發放貸款時對貸款投向國幾乎不加選擇。而由于條件設定的本身深受IMF的影響,也很難反映出借款國政府的真實意愿。 [14] 事后條件性貸款的信號作用在實踐中的效果不得不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四是其對“道德風險”的規避作用。條件的設定提高了借款國的借款成本,從而增強了各國在危機前采取防御措施的動機,減少了其因仰仗IMF的救助而怠于防御的可能性。但若IMF的條件只是擺設,無論條件是否得以執行,下一期的貸款仍會發放,借款國的動機就不會受到影響。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事實正是如此:IMF出于各種考慮,即使條件未得以執行,仍會選擇發放下一期貸款, [15] 這也就使得貸款條件理論上的規避作用在現實中難以實現。
鑒于實證研究的數據幾乎否定了貸款條件所有在理論上的作用,Dreher對貸款條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廢除現有的事后條件制度,以事前條件制度取而代之。
根據Dreher的模型,IMF應在非危機時期對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情況進行評估,并定期公開評估報告。危機時期各國所能獲得的貸款的數額和利率應根據其日常的經濟政策水平而定,二者如何掛鉤的標準也應在非危機時期予以公開。這樣,各國就會產生足夠的動機改善日常的經濟政策,并且可以避免事后條件的制約。
三、實踐中的運用
(一)臨時貸款安排(Contingent Credit Line,CCL)
IMF于1999年出臺的CCL是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事前條件性貸款項目。在該項目下取得貸款需通過資格審批和貸款啟動兩個階段。
IMF首先對申請國經濟政策的各方面進行評估,作出其是否有資格獲得貸款的決定,進而在申請國受到經濟危機波及而產生資金需要時進行貸款啟動的審核,以決定是否發放貸款。IMF希望通過該項目的實施,保證實施穩健經濟政策的國家在受到來自外部的經濟危機的波及時,能夠有足夠的資金渡過難關,并間接鼓勵各國采取更穩健的經濟政策和危機防范措施。 [16]
CCL與IMF的其他貸款項目不同:它以事前條件,即對借款國經濟政策的評估替代包括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各種事后條件;在申請該項目貸款時,申請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必須良好,不得有對資金的現實需要;且該項目只適用于受到金融危機傳染效應影響的國家,不包括危機原發國。從這個角度而言,CCL更接近于互補型模式,即事前條件性貸款只在特殊情況下使用,而并不適用于危機不具有外部傳染性,發生道德風險可能性較小的情況。
CCL在生效的5年內未被任何國家使用過,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非危機時期向IMF申請CCL項下的貸款,可能會給市場帶來經濟形勢惡化的錯覺,從而動搖市場信心,對該國的資本市場產生不利影響。若在取得CCL貸款后喪失資格,又可能給市場造成該國經濟政策出現問題的印象,同樣可能對資本市場產生負面影響。這就使申請國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無論是進是退,都有對市場信心產生不良影響的可能。二是CCL并未對申請國的貸款資格設置具體的標準,貸款資格的確定因而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其客觀性和公正性也更容易受到質疑。三是獲得貸款需要經歷資格審批和貸款啟動兩個階段,即使取得了貸款資格,也未必能夠獲得貸款。這一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不少國家望而卻步。四是CCL只適用來源于外部的傳染性危機,而在現實中,危機往往同時存在于經常項目下和資本項目下,并同時受到內部與外部的影響,很難嚴格區分。 [17]
CCL所存在的這些問題說明,一方面,事前性條件貸款由于其“信號作用”,可能對資本市場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有些影響甚至會與貸款項目的初衷背道而馳。事前條件性雖然避免了事后條件中最受詬病的結構性條件,卻因為難以對條件進行細化和量化,影響了條件的客觀性。另一方面,以是否具有外部性為標準對經濟危機進行區分在理論上或許很有吸引力,在現實中卻難以實現。倘若將事前條件性貸款僅僅限制在具有外部性的危機之內,可能使潛在申請國由于無法確定危機的類型而放棄提出貸款要求,也給IMF判斷具體情形是否屬于貸款項目的范圍加大了難度。
(二)靈活貸款安排(FCL)
IMF于2009年出臺的靈活貸款安排是事前條件性貸款的一次新嘗試。它取代了2008年出臺的SLF,取消了貸款上限,延長了貸款償付期間,并將適用范圍由危機處理擴大到危機防范和處理兩個階段。與CCL相同,此貸款項目不設任何事后性條件,而是以各國的經濟政策水平為標準,決定是否發放貸款。但與CCL相比,FCL又具有一些新特點:一是與CCL要求申請貸款時沒有危機迫近不同,FCL下的貸款可以在危機發生時申請,也可以作為預防性措施,在非危機時期申請。二是FCL的使用并不限于具有外部傳染性的危機,而是適用于任何類型的金融危機。三是FCL對國家經濟政策水平的審查以該國的貸款申請為前提,且在確定發放貸款之前嚴格向外界保密。相反,在CCL下,IMF在收到貸款申請之前就可能對潛在貸款國的政策狀況進行評估,且對是否將結果保密并無明確規定。四是FCL詳細規定了經濟政策水平的評估標準,但不對標準進行絕對量化,而是在綜合考慮各項因素的基礎之上作出最終評價。 [18]
FCL的這些新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CCL之前存在的問題。首先,貸款申請的保密性避免了其對市場的“信號效應”,使市場信心不會因為貸款申請和退出本身受到影響,從而打消了潛在申請國最大的顧慮。其次,FCL不要求對危機的類型作出明確判斷,IMF作出貸款決定的難度也就隨之降低。最后,明確的評估標準便于潛在申請國更準確地估計本國經濟政策水平,使其能夠更有的放矢地作出是否申請貸款的決定。對其他市場主體而言,也能更明確IMF同意或者拒絕貸款決定的原因,從而避免盲目行為,維持資本市場的穩定。與CCL遭到的冷遇不同,FCL出臺不到半年,就已經收到了包括墨西哥等三國的貸款申請。雖然不能否認金融危機這一客觀要素對各國資金需求的影響,但FCL的受歡迎程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其在現實中的可行性。
從設計結構上看,FCL更類似于Dreher所提出的模型,即將事前條件性貸款普遍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危機,且既可用于危機處理,又可用于危機防御。但從實質上看,FCL與Dreher的模型又有著根本的區別:在Dreher的模型下,事后條件性貸款應徹底為事前條件性貸款所取代,事前條件適用于所有成員國,并以事前條件為確定貸款數額和利率的主要標準。而FCL作為一個新型貸款項目,與傳統的事后條件性貸款項目并存,且由于申請資格的標準嚴格,能夠符合申請條件的國家也非常有限。從這個角度看,FCL仍是作為傳統事后條件性貸款的補充而非替代而存在的。
四、對本次貸款項目改革的評析
IMF在本次改革中出臺的FCL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都超越了之前的CCL,這說明IMF開始更為積極地使用事前條件性貸款這一貸款模式。但正如上文所述,FCL可適用的范圍相對有限,可見IMF并不愿貿然將事前條件性貸款鋪開,更遠未達到以其替代事后條件性貸款的地步。
IMF的謹慎可能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事前條件性貸款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不成熟性。首先,事前條件性貸款所設立的審查標準應包括哪些方面,各方面在最終決定上又應占到多大比重,這些都需要有成熟的經濟學理論作為支撐。事前條件性貸款將這些標準與各國所能獲得的貸款數額直接掛鉤,其與各國的利益相關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設置套具有足夠說服力的標準,事前條件性貸款的公正性與科學性也必然遭受公眾的質疑。另外,隨著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普適性逐漸遭到越來越多的懷疑。什么是真正“好的”經濟政策,這一問題的答案也越來越不確定。在這種情況下,由一套IMF自己設定的標準決定各國的命運,其合理性和正當性也自然需要更充分的論證。
其次,非危機時期對各國經濟政策的評估會對資本市場產生何種影響也需要進一步研究。雖然FCL通過對審查階段的保密緩解了各國對信號效應的顧慮,但如果事前條件性貸款擴大適用于所有成員國,保密也就不再具有可能性。如果按照Dreher的模型,將對各國的評估結果完全公開,其對市場影響的不確定性也會進一步增加。在深入研究結果出來之前,任何貿然的措施都有可能重蹈CCL的覆轍。
再次,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在危機發生后,即使成員國根據事前條件并不具備貸款資格,IMF也很難拒絕其要求。一方面,由于經濟危機的直接受害者是各國國民,而IMF很難置民眾的利益與國家社會的壓力于不顧。另一方面,IMF對各國經濟政策的監督和指導作用建立在與其長期合作關系的基礎之上。如果IMF在成員國危急時刻見死不救,則必然會對這一長期關系的延續產生不利的影響。當然,如果IMF只是減少貸款的數額,而非徹底拒絕提供貸款,是否能夠避免這些因素的作用,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19]
此外,雖然有大量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否附加貸款條件,借款國最終都會歸還IMF貸款, [20] 但以事前條件徹底替代事后條件,并適用于所有的成員國,其風險仍不容小覷。這也可能是IMF采取保守改革態度的原因之一。出于以上種種考慮,IMF僅對有限范圍內的國家適用事前條件性貸款也就不難理解了。
此次改革,IMF雙管齊下,一方面引入事前條件性貸款,另一方面繼續深化對事后條件性貸款的改革。
此舉看似砍柴磨刀兩不誤,但在筆者看來卻并非一勞永逸之舉。這是因為,FCL的高門檻意味著其只可能適用于少數經濟實力較強的新興國家,而眾多不發達國家則被拒之門外。這些國家經濟落后,經濟政策水平也相對低下,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達到取得FCL貸款申請資格所需的標準。事前條件性貸款的改革和FCL的引入對這些國家來說幾乎毫無意義,它們所能夠取得的貸款仍只有附帶結構性條件的傳統事后性貸款。IMF的改革既不能為它們帶來更多的資源,也不能起到鼓勵它們加強事前防御的作用。相反,IMF的公平性可能因此而從根本上遭到質疑。FCL的引入造成了差別待遇的客觀效果:經濟實力較強,經濟政策符合IMF評價標準的國家可以選擇事前條件性貸款在危機發生前就進行防范,且無須作出改變經濟政策的保證;而經濟實力較弱,經濟政策與“正統”標準不一致的國家則只能坐以待斃,并被迫接受可能包括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嚴苛的事后條件。如果說,過去國際社會對IMF采取雙重標準的批評還只是停留在個案上,FCL的局部適用將使這一批評擴大到IMF貸款框架的整體。 [21]
此外,根據FCL的設計,IMF對申請國貸款資格的評定建立在綜合考慮各項標準的基礎之上,從客觀上擴大了IMF的自主裁量權。且這一評價過程幾乎全程對外保密,IMF的決定因而更容易受到來自強權的影響。FCL出臺后,亞洲國家的反應一直較為冷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部分國家對于IMF仍持懷疑態度。
IMF若長期只在部分國家中適用事前條件性貸款,而對其他國家仍適用事后條件性貸款,勢必從根本上危及其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公平性。有鑒于此,筆者認為,IMF應將本次改革作為一次過渡,將FCL作為一個試驗性的貸款工具,根據其實施效果確定下一步改革的走向。倘若效果良好,則總結經驗,將事前條件性貸款擴大至所有成員;以統一的標準對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情況進行評估,并將評估結果與貸款數額和利率等掛鉤。這一評估可以與IMF現有的監督機制(Surveillance)相結合,也可以另起爐灶,建立新的評估機制。關鍵是,該評估須在所有成員國中進行,而非如目前FCL所實行的,僅以申請為前提在個別國家中進行。
五、結語
事前條件性貸款從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危機中孕育而生,從最初只適用于外部性危機的CCL,到2009年出臺的適用于所有危機類型,且既可用于危機防范又可用于危機解決的FCL,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理論界關于事前條件性貸款的原理,其與事后條件性貸款的關系,以及可能采取的形式等各種討論也從未間斷。從總的趨勢上看,事前條件性貸款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大,其內容設計也越來越成熟。隨著各國對事前條件性貸款了解的深入,敢于“吃螃蟹”的國家也越來越多。但是,目前的事前條件性貸款仍是作為事后條件性貸款的補充而存在的,其所采用的申請制和設置的高標準使其適用范圍受到了嚴格限制,從客觀上導致了對經濟實力和經濟政策水平不同的國家的差別對待。因此,FCL不可能長期存在,而應視為IMF對貸款項目深化改革的前奏。下一步的改革是前進(將事前條件性貸款在成員國中全面鋪開),還是后退(取消事前條件性貸款,仍沿用傳統的事后條件性貸款,只是對條件的具體內容進行改良),有待對FCL實施效果的進一步觀察。
尾注
康靜 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國際經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
[1] IMF Public Information Notice (PIN) No. 09/40, April3,.2009.
[2] 本文中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是指IMF成員國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他國利益的行為。
[3] Vaubel Roland.The Moral Hazard of IMF Lending,The World Economy (1983),pp.291 - 304;see also V aubel Ro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Ii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Tenth Henry Thornton Lecture (London: City University,1988).
[4] Cordella Tito, Eduardo Levy Yeyati, A (New) Country Insurance Factltty, IMF WorkingPaper05/23 (2005).
[5] Jonathan D. Ostry, Jeromin Zettelmeyer, Strengthening IMF Crisis Prevention, IMF work-ing paper 05/206 (2005) .
[6] Olivier Jeanne, Jonathan Ostry, Jeromin Zettelmeye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ristsLending and IMF Conditionality,IMF Working Paper No. 06/236, October 2008, p. 5.
[7] Axel Dreher, IMF conditionahty: theory and evidence, Public Choice Vol. 141 ( 1 ),October 2009, pp. 233 -267.
[8] Diwan I. , Rodrik D. , Debt reduction, adjustment lending, and burden sharing, NBERWorking Paper 4007 (1992) ; Sachs J., Conditionality, debt relief, and the deteloping country debtcrisis, In Sachs J (Ed.):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Vol .1.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Rodrik D. , Promises, promises: credible policy reform viasignaling, Economic Journal, 99 ( 1989 ) , pp. 756 - 772;. Fafchamps M. , Sovereign.debt,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conditiona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0 (1996), pp313 -
[9] Bird G. , Willett T. D. , IMF conditionalit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ownership,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6 (3) (2004), pp. 423 -450; Vreeland J.R. , The IMF: lender of last resort or scapegoat; Yale University,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1999) ; Drazen A. , Conditionality and ounership in IMF lending: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CEPR Discussion Paper 3562 (2002).
[10] Axel Dreher, IMF condition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Public Choice Vol. 141(1),October 2009,pp. 247-249.
[11] Khan M. S.,Shanna S., IMF conditionality and country ownership of programs, IMFIn-stitute, IMF (2001)
[12] Dreher A.,Thedevelopment of IMF and World Bank conditionality, In L. Yueh(Ed.),The law and ecónomics of globalisation: new challenges for a world in flux, Cheltenham: EdwardElgar (2009) Chapter 6; Spraos J.,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166.IMFconditionality: ineffectual,inefficient,mistargeted,Princeton: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
[13] Rodrik,D, Governing the World Economy: Does One Archttectural Style Fit All?, in:SCollins/n Lawrence (edds.), Brookings Trade Forum: 1999, Washington, D.C.: Brookings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 105-26.
[14] Bird G. , Rowlands D. , Financing balance of payments adjustment : options in the light ofthe illusory catalytic effect of IMF lending,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6 (3) (2004), pp.468-486.
[15] Killick, T. , Conditionality and IMF flexibility, In A. Paloni & M. Zanardi (Eds.), TheIMF, World Bank and policy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See also Vreeland, J. R. ,IMF program compliance: aggregate index versus policy specific research strateg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 (4) (2006), pp. 359-378.
[16] IMF Factsheet, The IMF's Contingent Credit Lines (CCL), March 2004.
[17] IMF, Review of Contingent Credit Lines, prepared by the StrategyPolicy and Review De-partment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departments, February 11, 2003.
[18] IMF, The Flexible Credit Line - Guidance on Operational Issues, prepared by the StrategyPolicy and Review Department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departments, November 02, 2009.
[19] Goldstein, M. , IMF. structural program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NBER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Mimeo (2000), pp. 68 -70.
[20] Axel Dreher, IMF condition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Public Choice Vol. 141 (1);October 2009, p. 243.
[21] Martin S. Edward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ditionality, and the WorldEconomic Crisis: New Beginning or False Dawn? See http://pirate. shu. edu/~edwardmb/condi-tionalityreform. pdf.
[1] IMF Public Information Notice (PIN) No. 09/40, April3,.2009.
[2] 本文中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是指IMF成員國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他國利益的行為。
[3] Vaubel Roland.The Moral Hazard of IMF Lending,The World Economy (1983),pp.291 - 304;see also V aubel Ro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Ii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Tenth Henry Thornton Lecture (London: City University,1988).
[4] Cordella Tito, Eduardo Levy Yeyati, A (New) Country Insurance Factltty, IMF WorkingPaper05/23 (2005).
[5] Jonathan D. Ostry, Jeromin Zettelmeyer, Strengthening IMF Crisis Prevention, IMF work-ing paper 05/206 (2005) .
[6] Olivier Jeanne, Jonathan Ostry, Jeromin Zettelmeye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ristsLending and IMF Conditionality,IMF Working Paper No. 06/236, October 2008, p. 5.
[7] Axel Dreher, IMF conditionahty: theory and evidence, Public Choice Vol. 141 ( 1 ),October 2009, pp. 233 -267.
[8] Diwan I. , Rodrik D. , Debt reduction, adjustment lending, and burden sharing, NBERWorking Paper 4007 (1992) ; Sachs J., Conditionality, debt relief, and the deteloping country debtcrisis, In Sachs J (Ed.):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Vol .1.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Rodrik D. , Promises, promises: credible policy reform viasignaling, Economic Journal, 99 ( 1989 ) , pp. 756 - 772;. Fafchamps M. , Sovereign.debt,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conditiona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0 (1996), pp313 -
[9] Bird G. , Willett T. D. , IMF conditionalit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ownership,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6 (3) (2004), pp. 423 -450; Vreeland J.R. , The IMF: lender of last resort or scapegoat; Yale University,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1999) ; Drazen A. , Conditionality and ounership in IMF lending: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CEPR Discussion Paper 3562 (2002).
[10] Axel Dreher, IMF condition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Public Choice Vol. 141(1),October 2009,pp. 247-249.
[11] Khan M. S.,Shanna S., IMF conditionality and country ownership of programs, IMFIn-stitute, IMF (2001)
[12] Dreher A.,Thedevelopment of IMF and World Bank conditionality, In L. Yueh(Ed.),The law and ecónomics of globalisation: new challenges for a world in flux, Cheltenham: EdwardElgar (2009) Chapter 6; Spraos J.,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166.IMFconditionality: ineffectual,inefficient,mistargeted,Princeton: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
[13] Rodrik,D, Governing the World Economy: Does One Archttectural Style Fit All?, in:SCollins/n Lawrence (edds.), Brookings Trade Forum: 1999, Washington, D.C.: Brookings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 105-26.
[14] Bird G. , Rowlands D. , Financing balance of payments adjustment : options in the light ofthe illusory catalytic effect of IMF lending,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6 (3) (2004), pp.468-486.
[15] Killick, T. , Conditionality and IMF flexibility, In A. Paloni & M. Zanardi (Eds.), TheIMF, World Bank and policy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See also Vreeland, J. R. ,IMF program compliance: aggregate index versus policy specific research strateg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 (4) (2006), pp. 359-378.
[16] IMF Factsheet, The IMF's Contingent Credit Lines (CCL), March 2004.
[17] IMF, Review of Contingent Credit Lines, prepared by the StrategyPolicy and Review De-partment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departments, February 11, 2003.
[18] IMF, The Flexible Credit Line - Guidance on Operational Issues, prepared by the StrategyPolicy and Review Department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departments, November 02, 2009.
[19] Goldstein, M. , IMF. structural program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NBER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Mimeo (2000), pp. 68 -70.
[20] Axel Dreher, IMF condition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Public Choice Vol. 141 (1);October 2009, p. 243.
[21] Martin S. Edward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ditionality, and the WorldEconomic Crisis: New Beginning or False Dawn? See http://pirate. shu. edu/~edwardmb/condi-tionalityreform.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