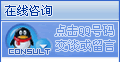一、問題的提出
在商業交易中經常使用的格式單一般由兩部分組成,正面是空格條款,即在預先印制這些條款時專門留下空位,使雙方可填入重要的合同細節,如他們所洽談的價格、質量、裝運日期等,背面則一般附有詳細的規定和標準條款。2正面條款是雙方當事人洽談的結果,一般不會發生分歧,背面的格式條款才是爭議的根源所在,格式之戰實質上也就是標準格式之戰。對于標準條款,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通則》)在第2.19條中下了一個標準的定義,其第2款規定“標準條款是指一方為通常和重復使用的目的而預先準備的條款,并在實際使用時未與對方談判。”該條款的注釋2進一步指出,對標準條款的理解,關鍵并不在于提出這種條款的形式(不論是包含在一個單獨的文件中還是包含在合同文件本身,也不論這些條款是以事先印好的格式發出,還是僅存于計算機內)、是由誰準備的(當事人自己、某一貿易或專業協會等)、內容如何(不論是幾乎包括合同所有相關方面的綜合性系列規定,還是僅僅關于一、兩個方面的規定,如責任的免除和仲裁),關鍵是這些條款為了通常和重復使用的目的已提前擬就,一方當事人在實際使用時未與對方談判,這后一項要求顯然只與那些對方當事人必須全部接受的標準條款有關,而同一合同中的其他條款正是當事人之間談判的主要內容。3
在現代商業交易中,使用標準格式合同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使用標準格式合同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省時間和花費,這也是最令商人們魂牽夢縈之所在。在從事同一類型的交易時使用事先預制好的標準格式合同可以避免每次交易時都為條款的設計花費時間和金錢,而且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疏漏,畢其功于一役豈不是商人們的上上之選?其次,使用標準格式合同有利于買賣雙方維護各自的利益。標準格式合同最大的文章就出在標準條款的設計上,雙方在各自的格式單中殫精竭慮地設計各種將自己的責任降到最小而將對方責任增到最大的標準條款,以期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對于標準格式合同的優點,有學者形象地指出:“在大規模生產的時代,幾乎沒有必要去強調大量生產的商品的優點,這與適用于其他事情一樣適用于大量生產的合同。”4然而,買賣雙方使用格式單在法律上制造的麻煩幾乎與其在商業上帶來的利益一樣多。在傳統的合同法理論適用的“鏡像規則”,要求承諾與要約的條款相一致,這正是格式之戰下所欠缺的。那么,問題就在于此時合同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則合同條款如何確定,特別是在雙方當事人做出履行行為之后,確認合同不成立已不具有現實意義的情況下如何確定合同的具體條款。各國立法、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圍繞著對“鏡像規則”的堅持與變革做出了不同的規定,在下面的幾個部分中分別予以具體的考察。
二、“鏡像規則”的堅持:CISG
“鏡像規則”是普通法上的傳統制度,1887年的Langellier v. Shaefer一案中曾對這一規則做出經典的歸納:“一方對另一方所發出的交易要約施加責任于前者,除非后者根據要約的條款對其予以承諾。任何對這些條款的修改和背離都將使要約無效,除非要約方同意這種修改和背離。”5英國法上至今還一直沿用傳統的“鏡像規則”,要求承諾嚴格地與要約相符,否則將被視為反要約。在著名的1979年Bulter v. Ex-Cell-O Corporation一案中,多數意見即是依據“鏡像規則”做出判決。傳統的“鏡像規則”與合同法一般理論中追求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價值取向相符,而且在實踐中具有兩方面的優勢。一方面,它提供了某種程度的確定性,合同的形式與真實的合同條款沒有差別,從而給當事人判斷他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個確切的標準;另一方面,這一規則提供了一個適用于所有類型合同的統一標準。但傳統的“鏡像規則”在面對現代商業交易中的格式之戰時則顯得過于嚴格和機械,它所采取的“全有或全無”的方式使得法官只能在買方或賣方的格式單中選擇其一而不能從真正的意義上去判斷雙方達成一致的條款,而且將會鼓勵當事人競相使用格式單并通過履行合同條件下的“最后一槍”理論爭取自己的格式單得以適用。6因此,許多國家的立法以及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在堅持“鏡像規則”的同時又對其進行微調,其中以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的規定較為典型。
CISG第19條第1款在一般規則的層面上嚴格地堅持了“鏡像規則”,規定“對要約表示承諾但載有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復,即為拒絕該項要約,并構成反要約。”第2款對一般規則進行了變通處理,規定“對要約表示承諾但載有添加或不同條件的答復,如所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在實質上并不變更該項要約的條件,除要約人在不過分遲延的時間內以口頭或書面通知反對其間的差異外,仍構成承諾。如果要約人不做出這種反對,合同的條件就以該項要約的條件以及承諾通知書中所載的更改為準。”第3款對“實質性變更”進行解釋,規定“有關貨物的價格、付款、貨物質量和數量、交貨地點和時間、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責任范圍或解決爭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條件,均視為在實質上變更要約的條件。”第19條規定了一般情況下對格式之戰的處理。從三款總體上看,CISG對“鏡像規則”的變通是非常有限的,雖然在第2款中開了一個口子,允許對要約進行非實質性變更且要約人未及時反對的承諾生效,并依照該承諾對要約的變動確定合同條款,但第3款對“實質性變更”的解釋幾乎涵蓋了合同所有的主要條款,使得“非實質性變更”在事實上是相當困難的,等于把口子大部分又給縫上了。而且,第3款的規定是非窮盡的,有學者將擔保條款、拒絕承認某事實的聲明條款、不可抗力條款、對違約救濟的限制責任條款等都列入“實質性變更”,7這樣更使得格式之戰下合同的成立難上加難。
在買賣雙方開始履行合同的情況下對于格式之戰的處理,CISG沒有專門的規定,但鑒于CISG將實質性變更的承諾視為反要約,那么第18條第3款關于以行為方式表示承諾的規定可適用于處理這一問題。第18條第3款規定“如果根據該項要約或依照當事人之間確立的習慣做法或慣例,被要約人可以做出某種行為,例如與發運貨物或支付價款有關的行為,來表示同意,而無須向要約人發出通知,則承諾于該項行為做出時生效,但該行為必須在第2款規定的期間內做出。”根據這一款的規定,在格式之戰中,特別是在買賣雙方不斷地互發格式單的情況下,最先履行并為對方所接受的行為可在合理預見的前提下構成對反要約的承諾,從而使合同成立。而在該行為做出前,行為方做收到的最后一份格式單將作為反要約而成為合同的條款,這也構成了CISG以“最后一槍為勝利者”的邏輯。
可見,CISG的規定并沒有解決傳統的“鏡像規則”在解決格式之戰時所存在的弊端。一方面,格式之戰下合同依然難以成立,限制條件過多;另一方面,“最后一槍”理論的采用更加劇了格式之戰的激烈程度,當事人為使自己的格式單成為合同條款而競相發出格式單以求自己贏得最后一槍,同時在確定合同條款時采取的非此即彼的方法仍無從確定雙方的合意之所在。因此,不得不指出,CISG對“鏡像規則”的變通和改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不成功的。
CISG的規定在各國立法例中很有代表性,也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國《合同法》第30、31條采納了CISG第19條的有限變通的“鏡像規則”,第22條規定了行為在存在習慣做法和慣例時也可構成承諾。大陸法系的合同法理論強調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與“鏡像規則”相合,法律中的規定也多與CISG相近。《歐洲合同法原則》第2.208條也是根據承諾對要約的變更是否具有實質性及要約人是否有條件限定或及時反對來判斷該承諾是否有效。8在德國法上,只有是對合同要約沒有限制的同意的表示,法律才認為是一項承諾表示,將要約擴大、縮小或作其他變更的承諾,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9根據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承諾表示僅限于其對要約為無限制的同意時,始被認為系屬承諾,將要約擴張、限制或變更而為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若原則上同意但卻希望有些微的變動或澄清的附加(非實體性變更),將此愿望告知要約人后要約人對新要約的沉默可因情況視為承諾,如所希望的附加或變動并不重要,他方承諾系屬意料中事。10
三、“鏡像規則”的變革:UCC
如果說CISG只是很有限地對“鏡像規則”進行變通的話,那么《美國統一商法典》(UCC)則在相當的程度上實現了對“鏡像規則”的變革,集中體現在UCC第2-207條的規定上。該條第1款規定“明確且及時表示的承諾或者在合理時間內發出的確認書生承諾之效力,即使它規定了與要約條款或雙方約定之條款不同的附加條款,但承諾人明確表示其承諾以要約人同意該附加條款或不同條款為條件的除外。”11這一款的規定廢棄了“鏡像規則”中承諾必須與要約相一致的要求,只要是明確及時的非限定性承諾即可生效,使得格式之戰下合同的成立較為容易。UCC考慮到,商人很少關心和閱讀合同背面的一般條件,視之為陳詞濫調,如果買方發出訂單,賣方發回銷售確認,只要雙方文件中的正面條件(品種、數量、價格)相符,即使背面條款不符,合同仍可成立。12UCC的此種考慮在格式之戰條件下是有其現實意義的,避免了大量正面條件已達成一致的合同因背面條款相歧而歸于不成立,或將它們成立與否歸因于此后捉摸不定的當事人行為,緩消了“鏡像規則”所表現出來的僵硬和機械,有利于商業交易的進行。但是,如果跳出格式之戰的視野,那么本款就會存在一個隱憂,就是非商人之間的交易,特別是商人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也一體承受這種變革的情況下是否有利于對消費者的保護,這已不是本文所考察的范圍,在此一提而過。
合同成立之后所面對的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合同條款的確定問題。UCC第2-207條第2款在一般情況下采用“第一槍”理論,規定“附加條款應解釋為補充合同之建議”,因此在要約方未對此建議表示認可的情況下,合同依要約的條款為準。但更為重要的是,第2款在一般規定之后做出了一個“商人特別規定”,即“在商人之間,此類條款構成合同內容,但以下情形除外:(a)要約明確規定承諾僅限于要約之條款的;(b)附加條款或者不同條款實質上改變了要約的;(c)要約人在收到有關此類條款的通知后于合理時間內發出異議通知的。”根據正式評論3,附加條款、不同條款均適用本款的規定。第2款中的這一“商人規定”主要即是針對格式之戰,采納了有限制的“最后一槍”理論,限制來自于對要約人意思的保護(a項和c項)以及非實質性變更的要求(b項)。前者屬慣常條款,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實質性變更”的問題。正式評論4指出,有些條款通常“實質性改變”了合同,如果在另一當事方未明確知悉時即被納入合同將會產生意外或極不公平的結果,典型的這類條款有否認一般性擔保的條款、在某種情況下要求保證交付90%或者100%的貨物的條款而行業慣例允許有更大數量的誤差、保留賣方在買方未能如期償付發票時取消合同的權力的條款、要求在比習慣所允許的時間或者比合理的時間短得多的時間內主張違約情形的條款。對于“實質性改變”的理解,有學者將其與商業慣例相聯系,指出“一個條款被認為是實質性改變,如果其與一般商業交易中的慣常條款有顯著不同,這一標準換言之就是將條款與主導的貿易習慣相比較。”13與CISG相比,UCC對“實質性變更”的理解顯然較為狹窄,僅限于某些對當事人根本性利益造成不利影響的重大條款,使得在較多的情況下,合同的條款依照承諾的變更確定。本款的規定在實質上仍未超出“鏡像規則”下非此即彼地確定合同條款的路數,只是單方面地傾向于將承諾的條款作為合同條款的基礎,不能說是在格式之戰下探尋雙方當事人合意的真實所在,不能真正地考慮到雙方的利益期待。UCC的這一規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瑞典及北歐國家的有關規定也與此相類似。14
第2-207條第3款針對履行行為成立合同做出安排,規定“盡管當事方之間的書面文件未能確定合同的存在,但雙方當事人承認合同存在之行為足以確定買賣合同的成立,此種情形下該特定合同之條款由與雙方的書面文件一致的條款和依據本法任何其他規定而納入合同的補充條款共同構成。”正式評論7的解釋中指出,“在許多場合,如在爭議產生前賣方已經發出了貨物,買方也接受了貨物并支付了價款的情形,不存在合同是否已經訂立的問題,在此類場合,當事人之間的書面材料未規定合同成立時,沒有必要決定哪一行為或文件構成要約,哪個構成承諾。”在這種書面材料不生效力的特殊情況下,UCC不得已拋棄了“非此即彼”的方法,轉向在雙方的書面文件中找尋相一致的條款并充分利用UCC的補充條款。第3款的規定雖然適用范圍非常有限,但在無意中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
真正將這一新思路綻放出光輝的則是2003年的UCC第2編修訂建議案。該修訂建議案對原UCC第2-207條的規定進行了徹底地修改。將原2-207條第1款移至修訂后的第2-206條,作為第3款并修改為“存在于書面材料的明確且及時表示的承諾生承諾之效力,即使它規定了與要約條款不同的或附加的條款”,并在正式評論2中明確指出廢棄“鏡像規則”。15較之原條文,強調了書面材料的存在,刪去了確認書的規定以及限制性承諾的規定,使得幾乎格式之戰下的所有承諾都可生效并成立合同。同時,更大的修改在新的2-207條,將條款名稱由“承諾或確認書的附加條款”改為“合同的條款;確認書的效力”,改寫了全部條文,新的規定為“根據第2-202條,如果(ⅰ)雙方當事人都承認合同的存在,雖然他們的書面材料未能確定合同,(ⅱ)合同通過要約和承諾形成,或(ⅲ)通過任何方式形成的合同由含有與已經確認的合同附加的或不同的條款的書面材料確認,合同的條款為:(a)出現在雙方書面材料中的條款;(b)無論存在書面材料與否,雙方當事人均同意的條款;與(c)依據本法任何規定補充或納入的條款。”修改后的條文首先不再區分一般規定與商人規定,在評論1中明確“本條適用于所有貨物買賣合同,不只限于存在格式之戰的合同”。其次,修改后的條文徹底否棄了原條文所采用的“非此即彼”方法,評論2中指出“本條不傾向于第一個或最后一個格式,對每個格式中的條款都適用相同的檢驗”,進而在評論3中意識到“在許多案件中,行為本身對于已經或將要發出自己的含有附加或不同條款的書面材料的當事人來說,不構成對另一方當事人的書面材料中條款的同意”。因此,修訂后的條文不再相信行為的推定作用,而是認真地去考察雙方當事人一致的意思并利用UCC的補充條款,這種對當事人一致意思的探求可通過雙方文件中的共同條款和雙方另行的共同意思表示進行,將原2-207條第3款在特殊情況下的方法擴大為一般的適用方法,糾正了傳統的“鏡像規則”下一直沿用的“非此即彼”方法,是格式之戰下確定合同條款的合適路徑。然而,同時應該看到,修訂建議案在這一問題上的處理方式顯得過于激進和簡單化。首先,合并一般規定與商人規定的做法值得商榷。原2-207條將二者分開規定的安排本來是UCC在處理格式之戰時較CISG更為合理之處,然而修訂后反而開了倒車,不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沒有考慮到商人之間交易與非商人之間交易的差別。其次,修訂后的第2-206條第3款進一步放寬了承諾生效的條件,有些過于激進,應當保留承諾方做出限制性承諾以避免某些重要條款落于合同之外的機會,仍應將此類限制性承諾視為反要約。同樣的道理,將要約方的及時反對權排斥于外也不利于保護要約方的利益。修訂條款的激進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過于偏重合同易于成立而忽視雙方的個體利益。
可見,無論是有限變革的原條款,還是激進變革的新條款,都不能完全適合于應對格式之戰的問題,仍然需要探尋一條對“鏡像規則”予以根本性變革但又不失穩健的解決方法。
四、穩健的變革:《通則》
盡管1979年的Butler案以沿用“鏡像規則”結案,但作為少數派的丹寧法官對此提出異議。他在1978年的Gibson v. Manchester City Council 一案中曾指出“認為所有的合同都可分析為要約和承諾形式的想法是錯誤的”,并提出“更好的方法是去查看當事人之間往來的文件并從這些文件或當事人的行為中搜集信息,判斷他們是否在實質問題上達成一致,即使文件的背面所印制的格式和條件不盡相同”。16丹寧法官提出的思路是可行的,同時還需要穩健的方式將其落實為具體的制度,CISG和UCC的嘗試都以有限的成果告終,而UCC的修訂建議案則激進得讓人無法接受。在這個問題上,《通則》的規定也許可以作為一個較好的范例。
《通則》在解決格式之戰時對其進行了特別化的處理,一方面在第2.11條中對變更的承諾做出一般性規定,另一方面根據格式之戰的具體情況在第2.22條中做出特別規定,沿襲了UCC原條文對商人之間與非商人之間區別處理的合理做法,并進一步明確為格式之戰與非格式之戰之分。應該說,對于非格式之戰下的變更性承諾,CISG第19條對“鏡像規則”的變通規定是合適的,在發出不存在標準條款的要約與承諾時,二者的一致還是尤為重要的,著實體現了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通則》將其引入作為第2.11條的一般規定是正確的,避免了UCC修訂建議案中那種簡單化的處理。
有關格式合同的問題,《通則》都做了特別化處理,第2.19條第1款規定“一方或雙方當事人使用標準格式條款訂立合同,適用訂立合同的一般規則,但應受到本章第2.20條至第2.22條的約束”,其中第2.22條即是格式之戰條款。第2.22條規定:“在雙方當事人均使用各自的標準條款的情況下,如果雙方對除標準條款以外的條款達成一致,則合同應根據已達成一致的條款以及在實質內容上相同的標準條款訂立,除非一方當事人已明確表示或事后毫不延遲地通知另一方當事人其不受此種合同的約束。”在注釋3中指出了“鏡像規則”對格式之戰的不適應性,即“通常當事人甚至不會注意到他們各自的標準條款之間存在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理由允許當事人在事后質疑合同的存在,或者如果當事人已開始履行,沒有理由非要堅持適用最后發出或引用的條款。”這一表述同時否定了“鏡像規則”下對要約、承諾一致性的要求和“非此即彼”的處理方式,超越了CISG和UCC原條款的規定。第2.22條采取了對雙方當事人真實的一致意思的探求來確定合同的條款,這與丹寧法官的思路相一致,也與修訂后的UCC第2-207條相近似。但與后者相比,《通則》第2.22條的規定存在過于簡單化的問題,只考慮了標準條款中實質內容上相同的條款,沒有考慮到當事人在格式合同之外通過文件或非文件的方式表示出的對某些標準條款的一致意思,因此應采取修訂后的UCC第2-207條(a)項和(b)項的規定更為合適,防止對當事人意思一致的考察有所疏漏。
《通則》第2.22條較之修訂后的UCC第2-206條第3款和第2-207條更為穩健和周全的一個方面就是保留了雙方當事人事先或事后作出“不受約束”聲明的權利,以防止由于某些重要條款落于合同之外而使當事人的個體利益受損,避免了修訂后的UCC條款過于偏重合同易于成立而忽視對當事人個體利益保護的缺陷。對于根據第2.22條確定的合同很可能會出現空缺條款的情況,《通則》第4.8條規定了補充空缺條款,即“如果合同當事人各方未能就一項確定其權利義務的重要條款達成一致,應補充一項適合于該情況的條款;在決定何為適當條款時,除其它因素外,應考慮以下情況:(a)各方當事人的意圖,(b)合同的性質與目的,(c)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則,(d)合理性。”與修訂后的UCC第2-206條第3款相比較,《通則》第2.22條還有一處不同,即后者要求當事人在對非標準條款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才可認定合同成立,前者無此要求。《通則》的這一規定顯然過于嚴格,對于非標準條款的意思一致問題應交由一般性規則處理,在格式之戰條款中規定非標準條款更有越俎代庖之嫌,因此采取“不能僅因標準條款沖突而認定合同不成立”的表述較為合適。
五、簡短的結論
通過對CISG、UCC和《通則》三個典型立法例的分析和比較,筆者認為,解決格式之戰問題的合適路徑至少應包含以下五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應將格式之戰與非格式之戰相區分,對格式之戰的問題做特別化處理;第二,在格式之戰條件下規定不能“不能僅因標準條款沖突而認定合同不成立”;第三,通過對當事人真實一致意思的考察而不是簡單地通過“非此即彼”的方法確定合同的條款,且考察不能僅通過對標準條款的比對,還應包括雙方當事人通過文件或非文件的方式表示出的對某些標準條款的一致意思;第四,賦予當事人事先或事后作出“不受約束”聲明的權利以保護其個體利益不致受損;第五,針對可能出現的條款空缺情況規定補充空缺條款。以上五點絕非完全穩妥的設計,也遠非問題的全部,解決格式之戰究竟路在何方,還需要我們繼續探求,但畢竟已經看到了方向。
參考書目:
1、阿狄亞著,趙旭東等譯:《合同法導論》(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2。
2、謝弗、厄爾、阿格斯蒂著,鄒建華主譯:《國際商法》(第四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
3、李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法律出版社,2002。
4、李先波:《合同有效成立比較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5、拉倫茨著,謝懷栻等譯:《德國民法通論》,法律出版社,2003。
6、黃立:《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7、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編譯:《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商事合同通則》,法律出版社,2002。
8、孫新強譯:《美國〈統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評論(二)》,載于《民商法論叢》(第21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
9、John Honnold, Uniform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s Under the 198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2.
10、Randy E. Barnett, Contracts: Cases and Doctrine (3rd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2003.
11、Ewan McKendrick, Contract Law(5th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m, 2003.
12、Clayton P. Gillette Steven D. Walt, Sales Law: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vised Edition), 2002.
13、Douglas G. Baird, Theodore Elsenberg, Thomas H. Jackson, Commercial and Debtor-Creditor Law: Selected Statutes (2003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03.
參考文獻:
1 See John Honnold, Uniform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s Under the 198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2,165.
2 謝弗、厄爾、阿格斯蒂著,鄒建華主譯:《國際商法》(第四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118。
3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編譯:《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商事合同通則》,法律出版社,2002,17.(以下《通則》條款的注釋從略。
4 阿狄亞著,趙旭東等譯:《合同法導論》(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2,17。
5 See Randy E. Barnett, Contracts: Cases and Doctrine (3rd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2003,321.
6 See Ewan McKendrick, Contract Law(5th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m, 2003,29。
7 李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法律出版社,2002,91。
8 李先波:《合同有效成立比較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68。
9 拉倫茨著,謝懷栻等譯:《德國民法通論》,法律出版社,2003,731。
10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75。
11 孫新強譯:《美國〈統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評論(二)》,載于《民商法論叢》(第21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785.(以下UCC條款及評論注釋從略)。
12 李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法律出版社,2002,92。
13 See Clayton P. Gillette Steven D. Walt, Sales Law: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vised Edition), 2002,73.
14 李先波:《合同有效成立比較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67。
15 See Douglas G. Baird, Theodore Elsenberg, Thomas H. Jackson, Commercial and Debtor-Creditor Law: Selected Statutes (2003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03,1225.(以下UCC第2編2003年修訂建議案條款及評論注釋從略)
16 See Ewan McKendrick, Contract Law(5th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m, 2003,30.
中國政法大學·陳韜